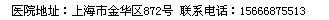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相关医院 > 罗爱伦一心一意为麻醉,一生一世协和人
罗爱伦一心一意为麻醉,一生一世协和人
有什么好方法治疗白癜风 http://baidianfeng.39.net/a_xcyy/130708/4206061.html
医院垂体疾病MDT团队访谈
她是国内外著名麻醉学专家、疼痛医学专家,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
她历任医院麻醉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麻醉学杂志总编辑、临床麻醉杂志副总编、比利时杨森科学委员会中国麻醉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她还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妇联执委。
她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扛过多次脑梗,但只要身体允许,医院上班。
她被医疗界的后辈们亲昵地称呼为“麻醉科女神”。
她就是医院麻醉科的罗爱伦教授。
年,罗爱伦教授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一名外文老师,她的名字“爱伦”就是英文“Allen”的谐音。她成长的那一条里弄里一共住着14户人家,在罗教授的印象中,许多邻居都是医学专业,不少还是留洋归来。她特别记得,4号住的是一位很有名的泌尿科专家。“他们平时都是用英文交流,我都听不懂的。”但她从不觉得自卑,“我常常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讲的东西我不懂就会问。”她还特别央求父亲教导她一些医学的英文生词,这对她后来的医学学习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这些学识渊博的邻居们就是罗教授对医生最初的印象。
念大学时,罗教授听从母亲的建议报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医院,“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北京,我以为我会在上海念完研究生。”临行前,母亲反复对她说:“你的职责是治疗患者,所以要对每一个患者认真负责。有不知道或者不懂的,你一定要向你认为最可靠的人请教。”母亲的谆谆教诲深深地烙印在罗教授心里,成为她行医五十六年里一直坚守的信念。
图1.罗爱伦教授年轻时照片
对病人一视同仁
“我的姨当年跟林巧稚大夫是很好的朋友,知道我要来协和,就把这张照片送给了我。”罗教授站起身绕过会议桌,随手拿起桌上花瓶中的装饰当作教杆,点了点挂在协和麻醉科贵宾接待室墙壁上的一张老照片,说道。
那是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里是当年的高干保健团队和一些重要的首长,包括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院士、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院士等重要人物。因为保健工作的保密性,罗教授一直仔细珍藏着这张照片,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决定把它拿出来,“我觉得还是要给年轻人看看,跟他们说一说那些以前的事情。”
图2.罗教授为我们指示图中的周恩来总理
后来,罗教授也成为了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从事了多年的高干保健工作。我们不愿去探听她曾救治过哪些重量级患者,她也绝口不提她曾担任过的治疗任务,但正如她母亲教诲的那般,罗教授五十六年来始终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做医生,服务对象都是患者,不管是首长还是普通人,都要关怀关爱他们,对他们负责,把他们治好。不管对象是谁,都不能有一些特殊的想法,要一律对待,一视同仁,服务好每一个患者。”
学习学习再学习
初到协和时,中国麻醉学科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而罗爱伦教授对麻醉更是非常陌生。于是,她下定决心要把麻醉学好,“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有事情都要弄懂。既然让你做了这个工作,你就要把它做好。”
对罗教授来说,毕业只是学习的开始。在繁忙的工作中,她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协和的图书馆看书学习。“协和是最好的学校,这里有三宝之一图书馆,想看的书、资料,这里都有。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分到这么好的地方。”
在协和,她学到的东西比在念书时还要多得多,来到协和短短一年,她已觉受益匪浅。这还得益于协和当时特殊的带教模式。“我医院里,三个人一间房,就在现在的护士楼。一个教授带两个年轻大夫。”而罗教授的带教教授是当时协和传染病组的组长王诗恒。“她对我们的爱护,现在想起都让我想流泪。”她回忆道,“王教授家住得远,平时都不回去,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总是说有什么问题晚上都可以问她,没有问题就去看书,直到有问题为止。遇到她也不确定的问题,她还会亲自去查阅资料,再跟我们讲解。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有这么好的老师,所以特别地珍惜时间。”
从那时起,医院里,把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对医院外的娱乐和诱惑置之不理。“我那时候休息都不回家,别人问我怎么不回家探亲,我就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实际上是说的谎话,我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向她们学习。”最后,还是常被她请教的教授们劝她回家休息,多出去玩玩。
直到现在,罗教授仍然保留着当年留下的习惯:每当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她就要用本子记下来,然后去请教或者查阅资料,从协和老专家到年轻大夫都是她的请教对象。“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懂不要紧,但一定不能不懂装懂,不懂装懂才是最可怕的。”在采访中,她多次强调“不懂就问”的重要性。
“协和确确实实是培养人的地方,我的成长离不开协和当时的环境和老一辈的教育。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这段历史,我要永远记着。”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类似的话罗教授反复说了三次,“我在业务上能有所收获,那都是协和给我的。”
图3.采访中的罗教授
一次协作一次收获
年,在史轶蘩院士的带领下,由神经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放射科、病理科、麻醉科、放疗科、计算机室等科室联合参与的《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中,麻醉科主导总结研究了《不同麻醉方式对经口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围术期生长激素的影响》。然而一开始,麻醉科其实并没有参与到课题小组中,还是现神经外科主任王任直教授的一句话改变了这一切。
“他就觉得虽然是做垂体,但是麻醉也是很重要的。他说,你们是麻醉大夫,你们也懂得很多垂体的东西。在做垂体的时候,麻醉做好和做不好会有不同的结果。你们应该研究这个问题,你们应该更好地总结每次手术,不是要找出缺点,而是总结每次做垂体肿瘤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有什么地方会影响到患者的生命指征。”王任直教授的话对罗教授来说犹如醍醐灌顶。
“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后来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注意观察。比如术中患者心脏跳得很厉害会引起什么,会给患者增加什么负担,会造成什么并发症,术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有问题,有时候觉着问题不大。有问题和没有问题的时候各应该怎么处理。”
因此,罗教授也特别喜欢跟其他科室合作:“每次他们喊我去合作,我都答应,而且特别高兴,因为有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情况其他科的同事会注意到,得到正确处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指导。”
先懂麻醉再做麻醉
医疗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外科大夫治病,麻醉大夫保命。”这是对麻醉医生重要性最为贴切的表达。然而,大多数患者对麻醉医生的认识还仍然停留在半世纪前辅助科室和医技人员的阶段,“麻醉师”这个称呼是让麻醉医生最无奈的别称。广东曾经有一项调查显示:约有90%等待手术的患者对麻醉医生的术前访视不理解。在许多患者,甚至部分医护人员的认知里,麻醉不过是插插管给点药的事。
对于这一点,罗教授深有感触:“很多人都觉得麻醉无所谓,甚至一些医生也这么想,随便把人麻倒了就行。但其实麻醉很重要,我不是因为这是我的专业才这么说。”麻醉那分寸之间精准的把握,才是麻醉医生的不可替代之处。
采访中,罗教授着重提及了麻醉医生的术前访视。她表示,术前,麻醉医生一定要对患者的重要脏器功能及整体生理状态进行全面了解,充分评估,这样才能制定出最适合患者的个性化麻醉方案,术中为患者的生命保驾护航,术后让患者更好更快康复。
“比如说一个患者,他的心脏二尖瓣有问题,如果麻醉大夫没有重视,没有做出相对应的麻醉方案,那么术中就有可能对患者心脏造成额外的负担,甚至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不幸。所谓不幸,我认为就是因为麻醉而给患者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麻醉大夫一定要细致,术前患者的情况一定要了解清楚,每一个小点都不能放过;术中监测也要细致,每一个变化都要重视。”对罗教授来说,懂麻醉,懂的不仅仅是麻醉操作技术、麻醉药物,还有每一次生命体征变化背后代表的意义和影响。
尽管行医一生,参与过的手术不计其数,但每一次术中患者生命体征发生变化,罗教授都格外重视,常常让同台的医生很不解。“他们说罗大夫胆小。其实罗大夫不是胆小,是真的觉得可怕。”她加重语气,“手术当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情况,就是处理不恰当,这是很危险的,应该重视,马上想办法纠正。”
罗教授的胆怯,来源于她对生命的敬畏,来源于医者对生命的珍爱。“我最怕他们说这没什么,很快就能纠正过来。那万一没纠正过来呢,这对患者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
为了更好地“懂麻醉”,罗教授一直致力于麻醉学的研究,对她来说,麻醉,是没有尽头的学习和发现。
她一生主持了数十种麻醉相关药物的Ⅱ期或Ⅲ临床试验,多次参加并主持国家和卫生部的重大科研项目并获奖;并先后开展了围手术期机体重要脏器如心、脑保护、嗜铬细胞瘤血流动力学及恶性高热基因分子生物学、麻醉药理及新药临床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麻醉学科领军人,她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麻醉学科在国际麻醉学界的地位和声誉。
罗教授还是国内最早推广疼痛治疗的先驱者,倡导和开展术后镇痛、晚期肿瘤镇痛及慢性疼痛治疗业务,使我国疼痛治疗向正规化、专业化发展。她率先引进了国外先进的镇痛方法如病人自控镇痛技术(Patientcontrolledanalgesia,PCA)、经皮给药镇痛等,以及疼痛治疗模式如术后急性疼痛治疗(Acutepainservice,APS)等,并通过开设疼痛门诊对各类慢性疼痛患者进行规范化、个体化治疗,大大推进了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
年,在原医院院长、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支持下,罗教授会同谢荣、赵俊等老专家提请了有关麻醉科独立建科的议案。同年5月3日,卫生部正式颁发第12号文件宣布:麻醉科正式独立于外科成为二级临床学科,。至此我国麻醉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今后中国麻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她对中国麻醉学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年英国皇家麻醉学院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迄今为止,只有两位中国麻醉医生获得过此荣誉,另一位获得者是中国麻醉学科奠基人谢荣。
“一个好的麻醉大夫一定要先懂麻醉再去做麻醉,要明白什么是麻醉,麻醉的内涵是什么,麻醉的不同结果会对患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懂了麻醉以后再做麻醉,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一辈子的麻醉生涯,没有因为麻醉而给患者增加负担,带来痛苦,造成不幸,只让他好上加好,这是我比较骄傲的一点。”
图4.上世纪80医院合影,从左到右,前排:罗爱伦、赵俊、罗来葵,后排:马遂、叶铁虎、高文华、任洪智、贾乃光
既是“严父”也是“慈母”
谈及罗爱伦教授,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这样评价道:“罗教授对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的最大贡献是规范了学会管理、把中国麻醉推向世界大舞台,而她对协和麻醉学科建设的最大贡献是造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和梯队。”
年,罗教授正式接任医院麻醉科工作,带领协和麻醉科走出十年动乱带来的负面影响,担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在任13年期间,她致力于科室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协和打造出国内最强大的麻醉人才梯队,培养了马遂、贾乃光、任洪智、高文华、叶铁虎、黄宇光等精英人才,协和麻醉科从一个只有10几个员工,8个手术间的小麻雀变成了多个工作人员和60多个手术间的庞然大物。
医院手术麻醉科主任赵晶教授来说,罗教授是她最尊敬的恩师。“罗老师是除了父母以外,对我最有恩的人。”她回忆道,“我95年到北京协和的时候,罗老师是麻醉科主任,我做麻醉都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她为人特别好,非常善良,但在专业上很严谨,要求特别严格。”
工作中要求严格,生活中关怀照顾,是所有受访者提及罗教授时都会说到的一点。在学生下属眼中,她同时兼任着“严父”、“慈母”这两个角色,让大家对她都又爱又怕。
在罗教授当主任期间,每天她都要认真地听交班,到每一个手术间去视察情况,了解当天的手术情况。麻醉科有一套通讯系统,用来通知麻醉医生手术安排。每当有紧急情况,只要广播一响,不管是不是罗教授负责,她都会亲临现场,指挥手术团队按部就班地抢救治疗。同时,她又非常善于发现问题,一旦发现疏忽错漏,就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教育,全心全意只为了守护患者的安全。
赵晶教授还记得,以前每次早上交班时,他们都要向罗教授汇报患者情况,罗教授会向他们提出一些特别细致的问题,常常让年轻医生们“措手不及”。“我还在做住院医师的时候,一次,罗老师问我们这个患者有没有得过青光眼,我们就觉得特别奇怪,因为麻醉和青光眼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原来,麻醉中常常会使用阿托品(Atropine),阿托品可能会引起患者的眼压升高,如果是患有青光眼的患者,则有可能会造成患者青光眼加重甚至导致失明的结果。”
罗教授的提问并没有因学生的疑惑而停下,她还进一步追问“患者患的是哪一型的青光眼,是闭角型还是开角型”,“是否经过手术治疗”,“在麻醉用药上会有什么影响,会造成什么不同后果”。赵教授还记得每次罗教授提问时那种紧张的感觉:“这种临床教学,极大地促进了我们。那时候我们不敢不知道,这次没答出来,回去就要赶紧学习,下一次好好准备。每次交班时压力都特别大,觉得自己回答不上罗老师的问题特别的不应该。”
正是罗教授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协和麻醉科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医生。赵晶表示:“是罗老师让我们明白,除了麻醉知识外,我们还要多了解患者的相关疾病和处理方法,及对患者转归的影响,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很全面的负责任的能保护患者围手术期间安全的麻醉科医生。”
同时,罗教授对学生和同事无微不至的关怀,却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年。”当问及罗教授的照顾,现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马上就想起了那一年。那时候还是研究生在读的黄宇光教授,跟着罗教授去广州参加全国麻醉年会。罗教授坐飞机先一步过去,而黄宇光教授则搭乘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我还刚结婚,打算开完会回安徽见家人。”
那时广州改革开放比北京早,黄教授万万没想到,在广州去逛街的公交车上,黄教授的钱包被偷了,钱包里除了自己的积蓄,还有同事委托他购物的资金。“我当时只能步行回会场,把事情原委告诉了罗教授。她说,你这样也没办法回家了,还是回北京去,我让科里多给你安排点手术,尽快把钱还上。”
当时,加台手术的费用是每个月大约元,但是是由科里轮流分配的,一个月下来大家的加班费都要差不多。在罗教授的帮助下,黄教授暂时脱离了这个轮班规则,有加台手术就尽量安排他上。“后来我连续加了3个月手术。我感觉遇到这个事情,罗教授跟我一样纠结,她很为我着想,还想办法帮我解决。而且,她还亲自打电话给我家人,医院有事无法回家的借口,没有惊动我的家人,让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小。”正是因为是这样一件小事,正是因为罗教授尽心尽力的帮助,黄宇光教授至今都印象深刻。
罗教授的“护犊”之心在协和是声名远播,只要是关系到科室同事的利益,她都要据理力争。为了让年轻大夫能安心工作,医院分房,她都为他们全力争取,甚至放弃自己的名额;为了培养科室人才,她为年轻人争取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甚至让出自己的机会,即便是重要科研成果,也常把年轻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甘做幕后英雄。
正是这样“严父慈母”般的教导和照顾,罗教授为协和麻醉科、为中国麻醉学界培养了一个个能撑起一片天的青年人才,协和麻醉科也仿佛一股拧紧的绳索,牢牢团结在一起。
图5.年罗爱伦教授和医院麻醉科部分同事在手术室合影
一心一意为协和
“对罗教授来说,协和就像她的家一样,所以不管大事小事,跟她有没有关系,她都要管。”黄宇光教授开玩笑道,“即便是院长,她也照样管。但她都是为了科室,医院,所以即便有时候脾气不太好,但大家都服她,也很尊敬她。”
王任直教授也对此印象深刻:“不只是麻醉科知道,医院其他人也知道。她没有私利,都是就事论事,从不会想说了管了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所以她没有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憋在肚子里,是个特别痛快的人。”
从食堂伙食到东西院合并,从停车场车位到门诊秩序,在罗教授的心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关不关她的事”、“会不会得罪人”。医院的事就是她的事,协和是她的家,协和的每一个同事都是她的家人。
“只要是本院职工的手术,不管认不认识,她都一定会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