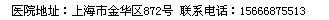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疾病病因 > 云南那邦田观鸟记
云南那邦田观鸟记
云南那邦田观鸟记
翻山越岭。
那邦藏在深山谷地,一条奔流,两个国度。从高黎贡山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来到此地,恍惚重归人间。
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本以为是边垂荒野的那邦小镇,居然宾馆林立、饭馆遍地。早知如此,前些年就该来。我们每每受制于自己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成为当下的囚徒,想来实在是可笑。
对面的缅甸最近正在闹内战,同行的十五说,若能听听枪炮声也算亲历战争该是多么刺激的事情。自然会被我们责骂,战争无情,死伤的都是人命。何况真要是战事逼近,我们来此观鸟的愿望也都会成了泡影,去年小苏来此便是如此。
正想着,对面馆子里传来夜鹭般哈哈哈的大笑声,不是小苏还能是谁?自从他厦大毕业后去了广州工作,我们就一只没有见过面,算是万里来相会了。此行云南观鸟,一路上不断遇到各地鸟友,不停地认识新鸟友。细细想来,缘分其实不是天注定,彼此心底都是同样的爱鸟心,自然心有灵犀。
那邦田已经没有田地,只剩下一条小溪、一条土路、和一点河滩湿地;剩下的,都已经是香蕉林了。当然,还有一条大河,隔着对面缅甸人骑着摩托车突突突的声响和孩子们嬉闹的笑声。据说这曾是一片神奇的田地,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鸟类出现在此,可如今田地已失,是否还能再续传奇?
带着忐忑的期待,我们踏着晨光中来此,山色与河流尚未从夜的梦中完全醒来,氤氲未散,宁静祥和。
忽然,对面的河滩上出现几位荷枪实弹的军人。隔着一条可以淌水而过的界河,寒光在军人背上的枪尖和腰上的刀刃上清晰可见。饶是我们知道两岸素来友好、相安无事,第一次近距离的遭遇还是让人不免有些激动,和一丝丝的不知所措。只是他们对我们的出现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继续着例行的巡逻,似乎还唱着歌。
我们到底还是觉得松了一口气,顺着他们离去的方向,望远镜里除了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石滩上又多了两个,不,是三个灰蓝色的身影——鹮嘴鷸——是除了我之外所有人的新目击纪录,刚才略显紧张的氛围转瞬间成了欢腾。沉浸在鹮嘴鷸如同圆月弯刀一般鲜红的大弯嘴和神奇的保护色中的我们,半晌才发觉裤脚早已被露水湿透,而阳光,也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开始炙热起来。
河滩湿地的草木有些地方茂盛的很,有些地方却相当稀疏。白斑黑石?爱在稀疏之处落脚,它果真天性坦荡,即便长得像个煤球,也照样喜欢站在众人面前。时间长了,倒也不觉得它难看,渐渐地竟然还有几分喜欢。毕竟就连马云看多了也会觉得顺眼许多不是?
草丛里另有一种大大方方的鸟儿,而且真的很大,大到即使有心理准备,等它真的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们竟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沼泽大尾莺,长得其实和棕扇尾莺没什么区别,只是后者比麻雀还娇小,它的块头却足以和灰喜鹊一拼了。莫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鸟,它才长成这样?据说东北人少年时期都会被送到山东过几个暑假,如此便可以长高个儿。我并不觉得个头大了有什么好,但潘长江也时常自嘲不是?!对着这个谈不上美丽,甚至完全破坏了我对莺莺燕燕吴侬软语所有美好想象的大鸟,我似乎也不能免俗,看不够似的紧盯着,嘴里还不是地叨咕着:“好大!好大!”可是,哎,我为什么要用赞叹的口气?
路边鲜有的几棵树上有鸟在跳,灰头黑喉,唯有耳后的栗色十分抢眼——栗颈噪鹛,难得一见的好鸟!并不像一般的噪鹛那么大胆,它们似乎很害羞,一直躲在树枝中间,等你刚刚看清楚,就急忙忙地飞远了。这是我们唯一一次与它们的相逢。或许缘分就这么多吧。已经知足了,尤其是后几天陆续遇到有别的鸟友询问我们是否遇见它们时候渴慕的眼神。
相比之下,不远处的绿喉蜂虎倒是挺大方,估计每一个来此的鸟友都或观或拍的不亦乐乎。相比较福建常见的栗喉蜂虎和蓝喉蜂虎,我更喜欢它,只因为胸口的那一抹春绿是如此动人,竟有些娇滴滴的若人爱怜。
天空中到处都是燕子,有几只在电线上停了下来,细看都是家燕。想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品种,好半天才发现有两只尾巴特别短的,瞪大眼睛再瞅,尾巴后面竟然还拖两根飘带,仿佛燕子风筝活了过来——这线尾燕果然名符其实。
凤头树燕也是这里的常客,它们是天空中快速闪过的大群芭蕾演员。细长的身段、灵动的舞姿,即便是四小天鹅的桥段与之相比,也简直是臃肿不堪。可惜的未能看到它们停歇下来的画面,无法一睹它最具魅力的额头上犹如两片树叶般精致的冠羽。不过既然从来到那邦的第一个瞬间开始,我便已经计划好了来年再来,错过,应该也只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逢吧。
天空中传来丛林鸦的叫声,缓缓地翅膀扇出一丝寒意,在它乌黑巨大的翅膀阴影地下,原本朗朗的晴空似乎也无能为力。一只亚成的蛇雕却好像白色的大天使,端坐在远处山边的树枝上,冷眼紧盯着眼前的一切。显然,它的眼神正告诉我,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期待。
那是什么?我们行走在高出河面的堤岸上,却惊起了临水的灌丛里一只硕大的深色鸟儿。不是池鹭,不是黑鳽,水面上反射的阳光让剪影变得难以辨认,但是心底却有了一个自己也不敢相信的答案。正欲确认一下,视线却被一间茅屋挡住。跑,必须赢过翅膀我们才有机会。可一过茅屋,可没想到又惊起一只大家伙——硕大的尾巴闪着墨绿色的光芒。幸亏我在海南见过它,瞥一眼就搞定了,不至于让绿嘴地鹃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狡猾同伙分了心。河面上那个真正“逃犯”,在它快速消失在长满水柳的河滩另一侧之前,它那大而突兀的眼睛还有耳后醒目的黑斑,被我的望远镜逮了个正着!bingo!海南鳽——猜测被证实了。
这是一种神秘的鸟儿,曾经以为几近灭绝,近年又陆续在华南多处被发现。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因为闯进了盗猎者的捕网才被发现的。种群数量依旧不容乐观的它们行动隐秘,能够在此与之不期而遇,实在是惊喜。这惊鸿一瞥,让我们的心底如饮了蜜一般甜了好久。
不过有人更爱喝的是可乐。史哥年方三七,性别不详,现在大四,马上研一,貌美肤白,拥趸无数。他与我一起撞见海南鳽,还发誓要帮我找到斑腰燕,因为之前我说过此行满了一百种新目击种就请大家吃饭。可是,据说当我不在的时候满天空都是的斑腰燕楞是不肯给我面子,直到后来去了瑞丽也都不曾遇见。于是,硬生生将拒我于千里之外,在当地其实算是寻常可见的鸟儿,折煞的似乎并不是我,而是史哥了。我最后还是愉快地请大家搓了一顿羊肉火锅,可那已经是在瑞丽的事情了。
史哥眼神不错,这一路上没少第一个发现鸟的身影;人也细心,将同行的大侠照顾得跟亲娘似的。史哥说其实他这次是第二次见我,我就想啊想,后来终于想起来是好几年前,他来厦门参见厦大绿野的观鸟培训营,听过我的一次课。只是当时我只顾着尽情卖弄,真没记住几个人。但是想来是卖弄得很成功,至少史哥记住了我。一开始他喊我老师,我觉得太别扭了——我哪里老嘛!再说,出门一起走,不分年龄,都是鸟友,还是叫山鹰听得舒服。
这几年,也不知道哪里刮来的妖风,观鸟、拍鸟的人中喜欢称呼对方“大师”,我因为资历也算比较老的,自然也听过。无论对方是开玩笑的还是恭维,都听得我毛骨悚然。不就是到野外走走看看鸟嘛,分明只是个找乐子的事情,冒充什么大师呢!可被人家叫得多了,渐渐地也有点麻木,冷不丁地还有点沾沾自喜的感觉,这才明白真所谓这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嗯,我还是学学那只在河滩上已经一动不动站立了半个小时的距翅麦鸡,冷静冷静的比较好。
继续说鸟。
那邦据说是目前国内最容易将五种燕尾一次性看全的地方。除了小燕尾个头娇小,其他四种除了羽色,体态习性都差不多:细嘴肥身,长长的尾巴像两根筷子支在身后,蠢蠢的可爱。燕尾习惯在石间跳跃或者沿着水流上下窜飞,溪流山涧是它们的食堂。白冠燕尾和灰背燕尾在福建都比较容易见到,斑背燕尾福建也有,却因为海拔较高,并不容易见。我错过很多次机会,一直不甘心。黑背燕尾只有西南才有,所以我自然也是没有见过的。我说过这次来云南之前我并没有做攻略,所以我并不知道那邦是看燕尾的好地方。直到“大推”告诉我。
“大推”和“大师”一样,也是虐称,大推是我们同行中最年轻的,二十岁不到,也是我遇到过最不靠谱的行动组织者,但是他也做了相当靠谱的一件事——就是把他自己想要看的鸟儿全都细致地做了功课——从声音到它们在各个鸟点出现的概率。学了那么多年鲁迅的文章,除了记得要“痛打落水狗”之外就是“拿来主义”了,好嘛!在他身上全用着了。
那邦田,一条流入界河的小溪里,黑背燕尾就在眼面前,四只。和石头底下的虫子相比,我们的出现显然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雪白的腹部和纯黑色的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天真的不懂夜的黑么?”黑背燕尾未必同意。这种在中国极其罕见的鸟儿,在我们完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这样被收获囊中,实在有点不过瘾的感觉。好歹学一学那斑背燕尾的矜持嘛,在那邦的数天里,高山峡谷间,斑背燕尾处处撩拨我的神经,却永远犹抱琵琶半遮面。直到我离开了那邦到了瑞丽,万念俱灰之际,它才现了真身,大秀其美,让我乐得差点儿就蹦了起来。人啊,怎么就是这么贱呢!
路边的湿地里,老黄牛静静地吃草,牛背鹭紧随左右,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本地居民大多不明白为何我们这些人爱来此凑热闹。其实还不是因为先有很多鸟儿喜欢来这里凑热闹呗!
八哥,哦不,是白领八哥。不像它那得了红眼病的大表哥,白领八哥戴着一副时髦的蓝色美瞳,肩羽上大块的白色好像围了一个硕大的白狐领子,为了扮贵妇,如此不嫌热也真是拼了!林八哥也冒了出来,它和八哥简直无法分别,不过是屁股底下少了几道囚服纹,便得意地好像果真是得了自由一般地到处纵声歌唱,引来红嘴椋鸟们粉丝似地跟在屁股后面不离左右。这红嘴椋鸟大约是借了丝光椋鸟闪若银丝的头羽,又将灰椋鸟的口红偷了过来,还学会了抹上蓝色的眼影。或许在椋鸟这个大家族里,大家见了它,都有些“吾家有女处长成”的娇宠和喜悦吧。
对我们而言,这三种鸟儿在国内均属罕见,但对于那些老牛,只怕早已是良朋美伴很多年了。有人说所谓旅行,就是去别人呆腻的地方看个新鲜。此话不假,但世界之大,既然有幸来走一遭,若总是蜗居一方,又怎知万态千相?世事确实恍如一梦,梦也应该多彩才是。纵然前世是云中仙如今遭贬人间,我也不着急回去。
话虽如此,故土总是难离,所以除了南来北往的候鸟,很多鸟和多数人一样,总是倦守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地。肉垂麦鸡,在我们走完了那邦田的沿河小路之时,依然没有见到它的影子。路并没有断,前方是座小山,大河绕山而去,是继续一探究竟还是回头?答案显而易见。
山路一侧竹茂林深,一侧下临湍流。山峦将原本宽阔的河床夹逼成窄道,对岸缅甸人家的对语清晰可闻。
不想,几个转弯处却豁然开朗,那河面中又冒出几处石滩,定睛一看,上面站立的正是肉垂麦鸡。于是小心翼翼辗转腾挪,不敢发出声响慢慢下到河床,然后又匍匐前行渐渐靠近目标。其实我怀疑当初我们如此谨慎根本没必要,因为一直到我们大摇大摆地离开,那些麦鸡都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呆若木鸡!像那些缅甸人,爱用一种植物的粉末抹在脸上额头,肉垂麦鸡也在脸上抹了一道白色的印迹,于此同时,又将眼线反过来画成一道红色的醒目连眉,异国的审美与我们差异如此之大,真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和麦鸡的安静不同,拥有一身纯粹的新绿色羽毛,和绿叶几乎融为一体的长嘴捕蛛鸟活泼多了。它那和身体差不多等长的细嘴不仅是啄食花蜜的利器,亦是密林里的结网待猎的蜘蛛们每天醒来后却不得不面对的恶梦。同行的越冬拍了一张它的倩影,我很喜欢——那是林中的翘望,是我们面对异域世界懵懂的眼神。
那邦田的界河上有一座吊桥,晃晃悠悠地没有任何阻碍你便可以由此“出国”。两岸来往的中国人、缅甸人,若不是文字标示和衣着服饰这些外在的东西,仅仅看脸庞,根本分不清楚。
身边缓缓掠过的白鹭,随着夕阳西下消失在对岸的山林;一只站立在缅甸基督教堂十字架上鹩哥,映在那邦农家的玻璃窗上,与窗后的佛龛融为一体。我忽然明白,令我们追逐飞羽至此的步伐戛然而止的,并非脚下的湍流和看不见的国界,而是那种在历史的错综复杂中深深的迷失感。能将人与国分开的是观念和权力,而不能分开的则是土地、河流和扎根其上一直流淌的血脉,以及,她所孕育出来的对自由永恒的向往。
愿生长翼,逡巡大地。
[完]
注:本文/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部分鸟类图片来自网络,若有版权异议,请联系本人删除。
山鹰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