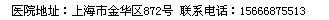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疾病知识 > Home原话蝴蝶骨和不可告人的夜话
Home原话蝴蝶骨和不可告人的夜话
历历万乡
作者丨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张晓真愿做白昼的月亮,虽不露锋芒,但不淆黑白。
1.你回山城的那日是04年的冬至日,深夜,无人接机,脚边只有一个笨重的棕色的旅行包。
夜晚的火车站,有着忽高忽低的男人的鼾声;还有小孩子夜里咿咿呀呀的声音,只是随后又无征兆的撕心裂肺的放声大哭;还有亲密的情侣你侬我侬的上演着琼瑶剧;路边有披着破旧的军大衣的小贩,双手环抱在胸前,半眯着一双困顿的眼睛,打着盹,偶尔发出几句叫卖声。
雪花簌簌的落着,铺了一地,天寒地冻。
你坐在角落里,身上穿了件显眼的粉红色羽绒服,袖子处还有领口,有显而易见的脏污,口袋处似也是因长久的掏弄,无法避免的秃噜了线头,咧了,像是一张哭泣的脸。
长久时间的坐车,使得你的面容略微有些浮肿,不知何时眼角的鱼尾纹已变得清晰,浓黑的眼袋写满倦意,还有那颤抖的扑闪扑闪的长黑色睫毛上挂着晶亮的泪珠。
在夜里,你背着包穿过一条条街道,那是拥堵的,充满汽车尾气以及生活垃圾味道的街道,那是有着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光的道路,路边有融化的黑色雪水集聚。
从94年到04年,你独自一人在外漂泊流浪,你到青藏朝圣,到陇西跪拜,你在新疆忏悔,到岭南赎罪,十年的岁月磨改,你自以为你丢掉有关这座城市的所有记忆,只是这里埋葬了你所有的温暖和爱,你终究选择了归来。
只是你呆在这座城市里,忍不住遍体生寒。
你走进“另域”——这里是另类人的地域,堕落的地狱。这里整夜整夜的笙歌,即使有人离开,它依旧毫不在意的释放着它的所有的激情和喧闹,它清楚,这里的生命力将永不断绝,总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带着欲望和兴奋,带着失意和沉闷踏入这里。
迷乱昏黄的灯光打在你的脸上,你哭的像个孩子,魅蓝色的眼影晕开,像只含冤的鬼魅,猩红的唇倔强的抿着。
你要了很多的酒,不管不顾的混在一起,喝的酩酊大醉,失去了神智,最后嘴里一遍遍地含糊不清的叫着“阿姐,阿姐。”
终至昏昏沉沉的睡去。
那个喝醉的夜晚,你睡得很香,你看到阿姐。年的山城,三十五岁的阿姐,二十岁的你。
2.你遇到阿姐的那次,受了男人的欺侮。
猥琐的老男人,有满嘴发黄的牙齿,腥臭的气味,已经秃了顶,露出油花花的头皮,身材发福,笨重的啤酒肚,总是说些下流的荤段子,眯着一双三角似的眼睛乱瞅,笑起来奸佞又残暴。
你的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烫伤,鞭伤,那是那个老男人的杰作,他确实是有那些奇诡的怪癖。
你趴在洗手间的池子上用手去抠自己的喉咙,吐得一塌糊涂,那些恶心的污秽物粘在你挑染的乱七八糟的头发丝上,泪水糊了满脸。
那真的不是你要的生活,却是你不得不妥协于现实,所能接受的生活。
阿姐喝的微醺,同男人纠缠着进了洗手间,看到了你,咯咯的笑起来,一张晕红的桃花面,还有一双晶亮的眼睛;还有那个男人,他猥琐的视线游走在你的身上,恶心感随即而来。
那个瞬间,你有被撞破狼狈状态的苦涩的羞辱感,还有怒涌的疯狂的嫉妒,你想要不顾一切的狠狠的同她吵一架,发泄心中的难受,可是阿姐却先是赶走了那个男人,走向了你。
“哟哟,好好的姑娘,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阿姐弯下腰将你搀扶起来,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绢,递给你,“喏,好歹也是个女孩子,怎么也要爱惜自己一些。”
“假惺惺的。”你梗着脖子,将她的手打掉,嘴角朝下一撇,重重的呼出一口气,不屑的来了一句,“靠,你他妈的神经病吧,在这里装什么好人,多管闲事,吃饱的撑得慌吧你。”
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时的你的故作不善只不过是你内心的自卑在作祟。
“小姑娘一个,说话这么冲,让你拿着就拿着,废话怎么这么多。”阿姐是真的喝醉了,她拿起手绢一边重重的在你的脸上擦拭着,一边飞快的说着:“不就是因为男人嘛,至于吗。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女人自己也可以过的快快乐乐的,离婚就离婚,有什么的啊,这算是什么事啊,干嘛非得女人被抛弃......”
最后她靠着你沉沉睡去,眼角有残余的眼泪。
那个时候,你恍然明白了一点:靠,TMD今天真是流年不利,这就算是遇到了个神经病。
3.后来,你便叫了她阿姐。
你越来越相信,女人最懂女人,女人才是女人的知己,女人才救得了女人
你哭喊着,将这些年来所有的委屈,一点点的倒出来,从你最单纯无垢的年龄到你最落魄狼狈的岁月,你将一切都告诉她。
只因她是你的阿姐,所以你愿意展现你所有的狼狈。
十六岁,你早恋,不听父母的劝告,被学校开除,然后跟着所谓的男友离开,来到南方山城,陌生的地域,你与男友同居,尖锐的争吵取代所有的稚嫩的爱情,一点点的发酵为恐惧和麻木。
你怀孕了,男友走了,你一个人走进那间小诊所,独自一人面对麻木的医生,还有那冰冷冷,阴泠泠的仪器,那时候的你甚至连打麻药的钱都出不起,你躺在手术椅上,望着那泛黄的房顶,墙体逐渐剥落,你仿佛望见一双黑黢黢的充满怨恨的眼睛。
你感到自己的孩子被一点点的剥离自己的身体,你疼很疼,像是被硬生生的割掉一半灵魂。
你哭的很惨,可你别无他法。
不过是不到17岁的年龄,你却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地狱,你的生活困顿潦倒,最后你只是一个卖笑的女人。
女人友谊的快速建立无外乎是同时仇恨一类事物,找到共同话题,再要不就是互相暴露伤口,彼此挟了把柄,互舔伤口。
你们的关系日益亲密,一起逛街,买一样的内衣,穿一样的衣服,戴着相同的首饰,你们亲密的手挽手,穿越大街小道,你们相视而笑,你们相拥而眠。
你们是姐妹,是朋友,更像是情侣。
你想,要是永远都有阿姐陪在身边,这一辈子,似乎也没遗憾了。
4.94年的重庆是什么样的呢?
街道破破烂烂,还尽是些平房,红色的墙壁上刷满各种标语。
入了夜的红灯区尽是些窈窕女郎,打扮的花枝招展,在深夜的街道上站着,裸露在外的长腿浮起细细密密的鸡皮疙瘩,只是那些女人极廉价。
来来往的人,不需要艳遇,看对了眼,一前一后走入附近廉价狭小的旅馆。那些旅馆环境肮脏,床单被褥上似乎还残留着上一对情侣的气味,墙壁不隔音,听得见那些细密隐私的声音。
不过只是一晚,潦草的完成一件事件,谁又会去在意呢?
近来的你开始抗拒别的男人的接触,你不想同他们虚与委蛇,不想笑的没有尊严,终于想要摆脱那些日夜颠倒的生活。
开始上街去寻找工作,刷盘子,做保姆,甚至想到了要去扛包,曾经那些你嫌弃脏累的活计,现在的你都想努力的试一试,你撕下所有的招工简报,小心翼翼的粘好,展开铺平,沓在一起。
其实你真的在努力的摆脱现在的生活,努力的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阿姐来找你时,哭的伤心,在你的住处摔酒瓶,她搂着你的脖子,凄凉而萎靡的神情,她说“那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的心,疼死了,疼死了!”她拉你的手放在胸脯上,直视着你的眼睛,“你感觉到了吗,我的心疼死了,我要离婚了,那个小三要进门了,我是个失败者。”
你们一瓶接一瓶的喝着酒,那也是腊月的冬夜,你的房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两个简单的热水袋,你们两个拥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来取暖。
那是和你一样的身体,女性独有的柔软纤细,她有干净的气味,她柔软的唇印在你的唇上,她有纤细柔嫩的手,她摸着你背上的伤疤,她说:“菁菁,肯定很疼吧。”
“疼。真的疼的。”
你最初的时候,被那些所谓的客人打,你就哭,撕心裂肺的哭,你一遍遍的喊疼,然后你记得他们狰狞的丑陋的脸庞愈加的兴奋,狂热的兴奋,你终于学会了笑,娇滴滴的笑,妩媚的笑,风骚的笑,所有的都虚伪的可怕。
后半夜,透过窗帘你看到外面泠泠的银光,世界美好的不可思议,你的心陷入一片柔软,你仿佛听到有轻柔的音乐在播放,你笑的不自知。
你偷偷的隔着一层被子搂住阿姐纤弱的肩膀,她有嶙峋的蝴蝶骨,你同她十指相扣,男女情人的模样,她的手温暖的,柔软的,那似乎是你一直追求的感觉。
温暖和爱......
冬夜的天,月光清澈明亮,将世界笼在一片银光之中,你一直睁着眼睛,不敢也不想去睡,想要看到冬日清晨的第一抹阳光,只是你终是等不得,依偎着阿姐,同那温暖的肉体,齐齐睡去。
终是没有等到那日的第一抹阳光。
5.山城总是氤氲着薄薄的白茫茫的雾气,看不见前方,最后只成了浓稠的带着腥气的艳红色的鲜血,那是你唯一的记忆。
那种有人关心,有人牵挂,那些温暖的日子,是你不想放弃的,你想信阿姐也是如此想的。
你和阿姐之间彼此默许了那晚的疯狂和迷乱,你们就是如此小心翼翼的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品尝着那些甜蜜又痛苦的温暖。
“菁菁,我们的未来在哪里。”阿姐的声音缥缈,带着不自觉的疲弱,她的眼睛有着深深的迷茫,黯淡的灰色,“没有人会认同我们的,他们将我们看做是怪物,我们不被承认啊。”
你哭着,因为抽噎,瘦弱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人一旦找到那根救命绳索,怎么肯轻易放弃,你抱着阿姐,“阿姐,我不要结束,我们可以等,我们可以偷偷的来往,我们也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只要不结束就可以。
“菁菁,我有家庭,我有孩子,即使我的婚姻走到尽头,但是我不想放弃我的孩子。”阿姐的话将你所有的自信击败,你放开她,咬着下唇,执拗的盯着阿姐的眼睛,努力的想要寻求一个答案,“所以阿姐,你是要放弃我,对吗?”
只是阿姐却先低下了头,闭了闭眼睛,她说:“别怪我,菁菁。别怪我,对不起。”
终是陷入了一室静默,窒息般的气氛。
7.
阿姐的名字叫顾新,我的妻子,04年我四十八岁,两鬓已经斑白,寡居,孩子已成家,一年回来一次。
我从未想过,你还会回到山城,并且找到我。
“当年,我的确逼迫了阿新,她是我的妻子,即使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但我不能忍受我的妻子和一个女人保持暧昧的关系,于是我拿孩子的抚养权逼迫她。”说到此,我的嘴角不禁染上了微笑,有些得意的意味,“阿新她是一个母亲,她无法放弃自己的孩子,所以林菁,她只能放弃你。我的确卑鄙,但是那个年代,你和阿新的爱情,我无法接受。”
你冷冷一笑,黝黑的眼珠有着显而易见的嘲讽,你将手中的茶水扫到地上,清晰的碎裂声,“你无法接受,你TMD凭什么无法接受,是你先背弃阿姐的,你要娶那个小三进门,你究竟有什么资格来说无法接受。”
你的口气太过无礼,让我忍不住也拍了桌子,“林菁,既然我没资格,你又凭什么跑到我的家来大放厥词。”
你盯着我,阴鸷冰冷的视线让我感到有一条吐着猩红信子的毒蛇在我的脖颈间盘旋,过了一会,你才开了口,“凭什么,就凭你当年强奸了我却没进监狱,就凭你逼死阿姐。”像是在说你的声音如此冷静,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那是别人的故事,而和你无关。
我在冰河上行走,我踏碎了冰,终是掉入冰冷的水中,我嘴唇颤抖着,脸色一寸寸变青变白,“林菁,我——”
你打断我,无悲无喜的说,“我还不知道阿姐的墓在哪里,你和我去一趟吧。”
墓地静的可怕,有些破败的枯草无精打采的伏趴在地上,西北风呼呼的吹着,有细碎的呻吟声,有疯狂的咆哮,交织成一首地狱的恶鬼游行的歌曲。
你跪在墓前,烧了很多的冥纸,黑色的灰烬夹杂着未燃尽的黄色冥纸在空中盘旋飞舞,还有那些细碎的火星,明明暗暗的闪烁着。
“阿姐,我从来没想过我还会在回到山城,这些年,我去了很多的城市,可是那些地方都没有你,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我太想你了。我告诉自己,只要哪天自己可以洗清那些罪孽,我就回来,给你烧冥纸,求取你的原谅,阿姐,你会原谅我的吧。”
你踉跄的起身,睁着一双水润的眸子,你声音温柔,“如果哪天我死了,我想要和阿姐葬在一起,而你会活很久很久,久到只剩下你一个,品尝那些孤寂的滋味,你说好不好。”
不等我回答,你看着空气,幽幽的说道,“阿姐,你莫要急,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那时候我就和你在一起好不好,你先忍忍呢。”
你笑,目光温柔,像是在看自己的情人。
8.
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诅咒的,而你就是那个下咒的恶毒女人。
那场墓地之行后,我们在回程的途中,发生了车祸,你重伤不治,盖上白布的那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你的嘴角弯出笑。
后来,我和阿新的儿子,发生了空难,外孙和儿媳离开。
而我一直活着,长久的活着,我一个人生活空荡荡的在夜晚听着电视发出聒噪的笑声,我真的很寂寞。
我的记忆再次回到以前,我在我生命的最后看到了阿新还有林菁。林菁曾经是我一夜情的对象,当她来到我家来找阿新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可她却是和阿新搞暧昧的女人,我说我要给她钱,要她离开,不过她竟然拒绝。
可笑,她不过是一个婊子,在恼怒之下我强奸了她。
只是,没想到阿新会看到那一切,阿新疯了。
她选择了自杀。
她柔嫩的白色身体躺在白色的放满水的浴缸里,纤细的手腕上有道深壑,鲜血凝固,眼睛半睁着,露出那双深灰色的黯淡的眸子。
又看到了林菁最后血肉模糊的模样。
我终于走到了生命的最后。
这座山城最后给我的记忆,只剩了浓稠的艳红色。作者: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张晓真原话车间总编:王丽君编辑:姜雁婕主编:崔一雯文化传播学院·新媒体中心北京中科医院电话北京哪治女性白癜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