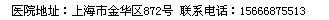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预防治疗 > 第一声妈妈
第一声妈妈
北京皲裂诚信医院讲解治疗办法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622593.html第一声妈妈
图/朱国智文/李世沛
每当鸡枞上市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地想念母亲,特别特别地想买很多很多的鸡枞来,炸成鸡枞油,让母亲在初一十五吃素的时候,有可口的下饭菜。让母亲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吃个够。当年,儿子工资不多,市场上也很少有鸡枞买,炸的不多,母亲用一个圆柱型的茶壶装着,吃素那天,拈一点点出来。因为太少,就那么一小茶壶,要靠它吃一年,12个月的初一十五,24天呐!我知道,母亲舍不得吃,母亲没有吃够。如今,市场上有,从娜姑运来卖的,大塑料袋装着,几十斤上百斤都有,儿子的工资也多了,一百斤一千斤鸡枞也买得起了,但母亲走了,吃不到了,儿子要尽这个孝也没有机会了。
母亲离开我们20年了。20年来,我对母亲最大的内疚就是没有买足够的鸡枞来给母亲吃个够!
母亲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的勤劳孝顺从小就铭刻在我的心上。因为家境贫寒,劳苦过度的祖父在我刚记事时就去世了。父亲长年在外,家里就是祖母和母亲推豆腐、扯挂面,起早贪黑地勤巴苦做,勉强地维持着三个人的最低生活。推豆腐是必须天不亮就起床的,头天晚上就发好的黄豆,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做出来的豆腐质量不好,因此不能睡过头。一升黄豆,少说也要两个来小时才能磨完。越磨得细,渣越少,豆腐的产量就越多,所以母亲总是小勺小勺地舀到磨眼里,每次也就10来颗吧。而且每次连豆舀到磨眼里的水也很少,水多,磨推起来就轻松,不费多少力,但沥下来的豆浆就很多、很清,涨(熬的意思)豆浆就很费柴火。水少,磨推起来就吃力,但涨豆浆就可以少费柴火。
母亲为节约柴火,就宁愿自己少睡一会,起早点,多受累,多吃苦,多磨一阵。豆子磨完了,还要过沥,还要把沥出的豆浆倒在大锅里烧开,然后才用磨好的石膏水倒入锅里“点”成豆花,然后才用豆花压成豆腐。这一切过程必须赶在八点左右完成,然后拿到街上去卖。如果要起豆腐皮,那就得通宵达旦地坐在灶门前,慢慢地往锅洞里添松毛结。火大了,豆浆就沸腾起来,结不成皮,严重的还会使豆浆潽到锅外,造成损失。一面还要注意着锅里的豆腐皮是否结得厚薄适中,即时挑起来。如果火候掌握不好,还会使豆腐皮产生一股焦味,外观也变得焦黄,既不好吃也不好看,严重影响销售。
母亲做的豆腐,压得很“老”,经得住挑剔的顾客用食指按,不像有的人家做的,晃当当的,一端起来就“塌方”,把膏水都当豆腐卖,欺骗顾客的钱。母亲说:“穷死也不赚黑良心的钱。”母亲起的豆腐皮,厚嘟嘟,板扎扎,色如凝脂,味比肉香,拿到市上,很好卖。如果做挂面,更是半夜三更就要起来揉面、盘面、上面棍、放入“醒槽”发酵,天亮时才能插上面坊拉扯。
母亲做的鸡蛋面,说是(一斤)两个鸡蛋,绝不少半滴蛋清,说是一斤一把(捆,包),绝不少一根。所以我家的产品,无论是豆腐、豆腐皮,还是面条,都非常受欢迎,不存在滞销之虑。
我在《铜商古都——会泽》和地方课程教材《读解会泽》中描写的迤车挂面:“面条细如棉线,金黄油亮。一根在手,颠闪不断;点火燃之,呼呼而终。煮在锅中,长时不浓;食余回锅,互不粘连。嚼于口中,筋骨毕现;一碗在桌,清香盈室。”写的就是母亲做的鸡蛋面!
母亲走了,我觉得迤车的鸡蛋挂面也变了。不说质量,单就数量而言,一把也就拇指般粗细,价钱也高得离谱。哎,如今这个世道,要钱的人太多太多,要良心的人太少太少!
因为母亲要半夜三更就起来磨豆腐扯面条,不能带年幼的儿子睡觉,所以我的幼年是奶奶带的。每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就听到灶房里哗啦哗啦的声音,那是母亲在推豆子了。我起床洗过脸,就站到灶边,看着大锅里慢慢涨起来的豆浆泡泡。一会儿锅开了,豆浆泡泡大部分散了,母亲就沿着锅边把没有散尽的豆浆泡泡,连同锅边刚结成的一小绺豆腐皮,舀在一个大碗中递给我。我接过母亲的碗来,放上一点盐,搅一搅,哎呀,那个味道,美得不可言传!我喝完这碗豆浆泡泡,就跳脚啰嗦地去玩了,而母亲的事情才做完一半。
人常说自古婆媳是天敌,人类社会,鲜有婆媳和睦的家庭。可是,搜遍我的记忆,找不到一次母亲与奶奶拌嘴的事。奶奶待母亲如亲生女儿,母亲孝奶奶如亲生之母。有段时间,奶奶左手疼痛,端碗都有困难,母亲寻医问药,端汤递水,经年伺候奶奶饮食起居,没有半句怨言。正所谓“婆婆有德媳妇贤”,母亲和奶奶的婆媳关系,有口皆碑,成为街坊四邻称道的典范。
母亲和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母亲凭着天生的聪颖和勤奋好学,掌握了上千个复杂多变的方块字,达到了可以读书写信的水平。
解放初期,农村兴起扫盲运动。我清楚记得,有天晚上,母亲从外面回来,手里拿了本《农民识字课本》,很高兴地说,不能再当“睁眼瞎”了,不识字,二天有事出远门,连厕所都找不到。母亲有空就去夜校,也不知是哪里学会的汉字偏旁部首,而且运用得很好。常常就着家里的“挂亮”(菜油灯)读《农民识字课本》,有不认识的字,就问我:“三点水着个某某字是读什么?”“双人旁着个某某字是读什么?”“草字头下面一个某某字是读什么?”并用笔很认真地写几遍。母亲还利用春节期间跟着唱书人学唱“小唱书”的机会学习认字。由于母亲学习刻苦,识的字越来越多,慢慢地可以自己独立唱完一本书了。《柳荫记》《蟒蛇记》《秦雪梅吊孝》《哭娘经》(母亲重新包装,自己写上书名的这本《哭娘经》我还珍藏着,看到它就像看到了母亲)都是母亲最喜爱的“小唱书”。
那个年代,冬闲的时候,农村没有什么文艺活动,更没有电视可看,妇女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聚到一起,听识字的人唱书。晚饭后,收洗罢,喂了猪,关好鸡,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围坐在火塘边,屏声静气地听母亲唱书。母亲的声音圆润悦耳,特别是“叠全十字”(唱书中十字一句的句子),非常优美(可惜母亲没有把她老人家的歌唱天赋遗传给我,我一辈子是“左嗓子”,唱不来歌,也不敢唱歌)。如果是唱《哭娘经》,会把怀念自己母亲的大妈大婶感染得泣不成声。母亲还曾自己提笔,一笔一划地给远在湖南工作的父亲写过信,也是给父亲报告自己的学习文化的成果。
我曾有过两个弟弟,都是“扯脐风”(新生儿破伤风病,多因脐带处理、消毒不严导致)夭折了,母亲把对儿子全部的爱都聚集在我的身上。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喊“左孃孃”的儿子死了,晚上,母亲带了我去看她。回家时,母亲一言不发,把我的手紧紧地捏着,像是怕我跑掉似的。
有好吃的,母亲自己舍不得吃,都要留给我。我小时候吃过的食物,有两次是终生难忘的。一次是不知谁送给奶奶一个“小白饼”(其实就是今天的白糖月饼,乡下没得买,要昆明才有,有卖也买不起),奶奶舍不得吃,有一天奶奶叫我到厨房里,从装碗的墙柜里拿了出来,切成两半,奶孙俩一人一半。那个小饼子又甜又香,甜,是清爽的甜,不像红糖那样有股浊味,香是玫瑰的清香。6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不可多得的甜香!另一次是母亲留给我的一碗青蒜炒臭豆腐。那时家里穷,不要说肉食,就是油煎油炒的菜也很难得,绝大多数日子就是苞谷饭淡白菜。
有时,我实在想吃米饭了,母亲就用小铜罐煨点米饭给我。由于家里没有一分水田,每一颗米都要靠奶奶和母亲用起五更睡半夜的辛劳去换取,所以这样的情况也不多,记忆中只有几次。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时,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说她和奶奶吃掉了,饭菜在灶屋头叫我自己去吃。我跑进灶房,见罗锅中的是米饭,火塘中的三脚旁扣着一个大碗,用热灰中的“姊妹火”焐着保温。揭开扣在上面的小碗,是青蒜苗炒的臭豆腐,油汪汪的。哎呀,那个香呀,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也难以用笔墨描写!朴素地说,以前没有吃过那么美味可口的青蒜苗炒的臭豆腐,以后也没有吃过。当时我没有多想,一口气全吃完了。现在想来,母亲从来都是等儿子放学回来才一起吃饭,这回却说先吃了,一定是故意把这碗好菜留下给我一个人吃的。
自我离家读书,每逢假期回家,母亲就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拿出来煮。我在家的一个假期,我们家真是“油锅不响不吃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母亲那因常年劳累、营养不良而缺少血色的脸,渐渐地泛起了红晕。不用说,首先是因儿子回家的喜悦心情的滋养,其次才是因儿子回家营养的改善,总之都是儿子的原因。
年,我从会泽中学初中毕业,因头年会泽县划归新成立的东川市,会泽中学改名“东川市第三中学”。中考便由全市统一录取,我和其他七位同学录取到“东川市第一中学”,校址在东川市政府和东川矿务局机关所在地汤丹。那里最高海拔米,气温比会泽低得多。会泽的冬天就够冷了,常记得上午坐在教室里上课,脚趾头冻僵得生疼。也没有棉衣,单衣薄裤熬过了初中三年。到东川就实在难熬了,没有抵御严寒的棉衣,也没有厚一点的床垫,只有叔叔(我喊“小耶”)当兵回家带回来的一条磨光了毛的线毯和一层垫单。夜晚,冷风从床板缝隙中钻上来,把我从熟睡中生生冻醒。
再加上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餐只有一平碗掺了一半红豆的饭,菜更缺油少盐,常常感到饥饿难忍。有一次,学校也是好心,为给全校学生填饱一回成年累月瘪着的肚子,以一斤大米换四斤洋芋的交易,与附近生产队换来了一顿数量使大家欢欣鼓舞的晚饭。但这些洋芋都已变绿,又苦又麻,我们实在是“饥不择食”,蘸着盐巴把分到手的洋芋统统吃光。肚子是吃饱了,睡到夜间,全校学生上吐下泻,来了个集体食物中毒。
母亲生怕我应了那句“又冷又饿,快当不过”的俗话,尽管家里也没有吃的,母亲和奶奶也在挨饿,但母亲还是把她和奶奶口里省下的苞谷炒熟了推成面带给我,又从信用社借得八块钱,在供销社买了件布纽袢的黑色棉衣寄给我。有了这件厚实的新棉衣,东川的冬天不冷了。
我在母亲的关怀下顺利完成了三年的高中学业,抱着一定要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决心,发奋苦读。在年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省18所大学压为7所,全国高考招生由年的人,录取率78.85%,调整为年的人,录取率24.32%的严峻形势下,我仍以第二志愿录取于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靠的就是母亲的关爱和报答母亲的动力。
说到报答母亲,我稍许得点安慰。母亲体弱多病,我就给母亲买红参。母亲总舍不得多吃,我每年探亲假回家,总看到母亲的床头柜上那个小筲箕里装着的红参,足有二三十根。我在昆明给母亲买的一双尖角黑皮鞋,正合母亲穿。母亲穿上这双鞋,在老姊妹们面前很有脸面,都说母亲有福,儿子孝道。我到北戴河疗养,特意在北京王府井绸缎庄给母亲挑选了一段很漂亮的绸子,要母亲用来做件外衣,但母亲一直舍不得,直到母亲去世也没有用。
我总觉得孝敬母亲的太少太少,尤其是想到母亲没有足够的油鸡枞下饭,是我终身无法消除的巨大的内疚和痛苦!虽然我对母亲尽了一分孝,但竭尽寸草心,难报三春晖!
我常想:为给我买那件小棉衣,母亲不知付出多少辛劳,才赔还了信用社的八元贷款。就是那件棉衣,陪我从汤丹的穷乡僻壤,跨入云南的省会都市,进入昆明的高等学府,她像母亲一样,看着我读完大学,走进社会。年,我才用工资买了件可以拆开洗涤的披领“干部服”棉衣。现在,我明显地感觉到,无论是我的加厚雪花呢长、短大衣,还是“波司登”等名牌羽绒服;也无论是女儿买的水貂毛领、皮毛胆的外套,还是我的老同学张明智送的美国≡SPRIT商标的保暖外衣和背心,穿在身上,都没有当年母亲买的那件“农民式”的小棉衣暖和。
大约在我高二的春季学期结束时,一天早上,忽然鼻内流血,而且怎么也止不住。我躺在床上,侧身把头伸到床外,看着一滴一滴的血慢慢把木床的床脚都淹着了,我却毫无办法。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因为已经放假,我就匆匆赶回家。我回到家,却不见母亲。奶奶说,母亲听说我病了,前天就走路去东川瞧我去了。因为那时迤车到会泽还没有班车,更不要说到东川。要坐车进城,只有求饭店的人帮忙,因为驾驶员总要在饭店吃饭,可以请路过的货车带上,但成功率很小,而且时间也没有定准。母亲心急如焚,当然等不得找货车,背上几斤米就走路去看我了。也是皇天有眼,母亲居然找到了一个同行的女伴,不孤单,也不用担心走错路,天一亮就上路了。
母亲小时候裹过脚,后来“放”了,但已不是天足,走路自然受影响,特别是走长途。母亲挂着儿子的病情,巴不得飞到儿子身边,自然不顾一切。从迤车到会泽,两个马站,里,健康的男子汉都要走两天。母亲起早贪黑,一天走10来个小时,硬是两天走到会泽,又从会泽两天走到汤丹。八月间的小江边,骄阳似火,母亲喉咙干得冒烟,在泥石流淤积的江面上精疲力尽,踉踉跄跄地艰难前行,为的是早一分钟见到儿子。可是当母亲千辛万苦到达学校时,儿子已经回家了。母亲确知儿子病好回家,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翻山越岭,走了整整四天的路,却没能见到儿子;喜的是儿子的病已经好了,已经回家了!母亲一天也没有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往回赶,怕的是儿子挂念!
母亲回到家时,拿出来几斤红皮花生。家乡迤车不产花生,母亲知道儿子最爱吃花生,回来时在小江用带在路上吃的米跟住店的房东换了花生,背着走了两百来里路给儿子带回来。
母亲,一点一滴,一分一秒,每走一步,每过一天,都在想着儿子!
我小时不乖,常生病,母亲按照算命先生指点,让我拜祭了好几个“老干爹”,其中一个还是从梁山搬下来不久的彝族,甚至还有一棵大槐树。并且不能叫自己的父母为“爹”“妈”,要把“爹”喊做“老爸”,把“妈”喊做“婶婶”。直到母亲去世,54年,我都是叫“婶婶”,没有叫过一声“妈”,我好后悔好后悔!如今,我再不信算命先生的胡说八道,我要叫我的母亲千声万声“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您听到了吗?我的妈妈!
.10.6.21:36一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