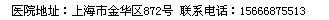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预防治疗 > 吴亦凡回家封面故事
吴亦凡回家封面故事
文|季艺
采访|季艺顾玥
编辑|张捷
摄影|王龙伟
沉默的孩子
年,看着温哥华列治文的别墅渐渐适宜生活,吴亦凡的母亲第一次感到稳定和满足。她似乎能在这座房子里看到一条漫长之路即将走上正轨:17岁的儿子第二年会从这里考上大学,进入社会,按照她为他设定的目标成为一名医生,结婚生子,她则完成抚养任务,迎来解脱,「然后我们就过着这种稳定的生活。」她说。
比起那座房子,吴亦凡有时更需要的是房子外面那条小路,这让他在感到压抑时,可以起身离开,通过不断行走和独处重获平静。
「确实有段时间我很叛逆,离家出走有过。」吴亦凡把这称为「离家出走」。但是吴妈妈不记得儿子曾经离家出走,多年后,听到《人物》记者的转述,她有些惊讶,「他可能觉得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但是他走的可能就是出去转了一圈。」她想了想,说。
「转了一圈」在高考临近时越来越频繁,在一种走投无路的情绪中,吴亦凡看到的是和母亲完全不同的画面。
他认为和母亲的关系正走向破裂,他们的家摇摇欲坠,「不是能够让我好好去过的一个家庭了。」他对《人物》记者回忆,「我觉得我需要去帮助这个家,这种使命感特别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我必须得站出来。」
从出生开始,吴亦凡基本就是母亲独自带大的。失去婚姻那一年,年,30出头的母亲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她决心让10岁的儿子跟随自己的姓氏,把所有生活奉献给他。
这包括为了让他享受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带他从广州来到温哥华,开始了需要背井离乡近10年才能获得身份的移民路;花3年往返国内最终关掉曾经拥有的企业,彻底成为再无收入的家庭主妇;其代价还有为避免儿子产生这不再是自己家的感觉,保证自己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在他18岁上大学之前,她要求自己绝不允许第二个男人出现在这个家中,她担心任何不可控的因素影响儿子的成长。
两个小时采访中,「稳定」是吴妈妈常常脱口而出的关键词之一,共有7次。专心沉浸在抚养儿子中的吴妈妈鲜少与外界发生关系,从不参加温哥华当地华人的社团活动,只有一位当地妇女会会长才能差使她走出家门。在她刚来此地举目无亲想要赶快买下房产开始生活却找不到律师时,会长伸出过援助之手,那次雪中送炭令她至今感恩。
从那次孤注一掷直到现在,她的生活和担忧时刻为伴。在加拿大,她排斥一切复杂、肮脏的东西进入她和儿子的房子。很长一段时间,儿子跟什么人接触,她都会亲自去问,如果发现这个人有点问题,她要想出办法阻挠。「其实可能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会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
她开始变得「总是啰啰嗦嗦的」,「动不动一看到什么,就开始教育,别人发生了一件事情,拿回来给儿子一顿说教之类,就总是这样。」
她相信受苦会令儿子更加努力。在她的观念里,男孩子应该有责任感,她的教育方式是告诉儿子你要独立,18岁自立。这也是她某种程度上不想依靠他人而独自抚养吴亦凡的理由,虽然自己会辛苦一点,但她认为这种辛苦会让儿子意识到「要孝顺妈妈」,更早产生责任感。
吴亦凡13岁那年,吴妈妈忽然发现他比自己高了,家里再遇到一些事时,她下意识地说,这个事是应该你们男人做的,「然后人家就不吭声就去做了。」说这话时,对面的《人物》记者感受到了她的骄傲与欣慰,「特别好玩,」她说,但随后她又有些不安,「他才13岁啊。」
这个男孩过早的沉默曾给吴妈妈的好友Sindy留下深刻印象和某种不安。年12月,坐在《人物》记者对面,Sindy回忆起女友讲述儿子的场景,她记得在女友的讲述中,这个男孩的形象常是沉默的。「凡凡就不说话」,Sindy对《人物》记者说。
让她印象深刻的一次,女友说起看到儿子没有按时休息,还坐在电脑前沉迷网络游戏时,女友没有说任何话,「啪」地一下把电脑关掉。「好过分啊」,Sindy记得自己对女友说,「我说我妈妈这样对我,我非发一顿脾气不可,不管怎么样在玩的兴头上,啪就给关了。」Sindy靠在椅背上,眉头皱了起来。
她想了想如果这件事放在其他孩子身上,也应该早就闹了,但同龄人的正常反应吴亦凡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他基本上就是,他不会吵也不会闹……他就不说话。」
不过,她没让自己按照这种疑惑多想下去,而是用一种中国式懂事表扬了他,「我觉得他挺独立的」,「心理啊」,「还有他生活上都是蛮独立的」。
年,刚到加拿大的吴亦凡面临英语入学考试,当听说别人家的孩子两三年都无法通过时,吴妈妈陷入习惯性焦虑,「我就不间断地说,你背英语单词啊,要不然你过不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就老是嘟囔人家,你不过怎么怎么样……他没有考试之前我就一直折磨他……这一年我就在折磨他。」
10岁的吴亦凡没有说一句话。发现儿子没有表现得和自己一样紧张,母亲又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没有听懂,「不吭声我就认为他没说懂,我就换个方式再说,还不吭声我就再换一个方式再说。」
虽未如母亲期待的那般努力,但那次英语考试很早就开始准备的吴亦凡第一次就过了。不过这个男孩并未得到应有的表扬,不表扬是因为母亲担心失去控制力,「我不可能和他去唱红脸的,我就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我要管他,我就拿出那一点威严来,要不然他就觉得就没效果或者什么的,我就会这样想。」她告诉《人物》记者。
鸡汤凡
年代的广州,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男孩,因家人工作繁忙而不得不在游泳课上消磨暑假。吴亦凡至今记得当时和其他小朋友一同站在游泳池前看到的景象。那时,那座湿热的南方城市刚下过雨,水面上漂着很多树叶,整个池里的水全都特别的混浊。但当教练说跳下去时,那天,他是唯一毫不犹豫跳进脏水的小朋友。第二天,他医院。
「我就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没什么事,是你们不敢跳而已,我就敢跳,我就跳了。」近20年后的现在,回忆起那时的勇气,吴亦凡说,「我不太愿意让别人失望,尤其是长辈。」
吴亦凡不希望自己是弱小的。在对自己的高期望中,面对移民,他远不像母亲以为的那么平静,而是面对巨大的成长危机。吴亦凡的童年,从老家甘肃白银,到广州,再到温哥华,一直在不断的移动转学搬家。因为老是换学校,小伙伴刚玩得好就又要去交新朋友,每天吃午饭对于吴亦凡而言是非常尴尬的时刻,看着其他小朋友特别熟地聚在一起吃,他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这让他有段时间「非常内向,非常自闭」。「不是一个交际花,从来不是一个交际特别好的人。」他说,「我小时候特别希望成为一个中心,谁不希望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呢,尤其是男孩子。」
吴亦凡没有把这个苦恼告诉母亲,他怕增加母亲的担心,想一个人硬扛下来。
硬扛的结果是他至今有一个习惯,遇到不知道怎么办的事第一想到的不是问问身边人,而是看看励志书里有没有教过。母亲是他那时唯一的沟通通道,但自己把这个通道封闭起来后,他只能去街上逛书店买回那些排行榜上的热门书籍,「什么书我都看」,「中文的、英文的都看过」。大多是励志书,如何说话、如何做人、如何观察别人、身体语言。他想从上面找到让自己受欢迎的方法。看到哪里就感觉「这个我明天可以试一下」。「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吴亦凡笑着对《人物》记者说。
比如,对陌生人微笑打招呼会拉近人和人的距离,书里就是这么告诉他的。直到现在,吴亦凡见人永远带着笑容。「见到谁都是笑,已经习惯了,我相信你这样对别人,别人也会这样对你,最起码不会讨厌你。而且笑容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我觉得友善的感觉是互相的。」
长期面对着励志书自我成长,让吴亦凡后来得了一个外号,「鸡汤凡」。
篮球的出现是吴亦凡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通。吴亦凡15岁那年,因为处理国内最后的事务,母亲带着儿子回广州一年,由于温哥华教学和国内不同,吴亦凡回广州上的是体校,打的是篮球。他是球队队长,打的位置是控球后卫,把控一些战术走向的角色,很多时候需要把球贡献给队友,照顾大局。他很喜欢这个角色,「队友得分的时候,你也会有那种喜悦感。」
在吴亦凡看来,喜欢上篮球对他的内心有本质改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我释放,找到小伙伴,自然而然地找到与人沟通的方式。更重要的,也是在那时,他第一次发现了他后来认定的自己性格中「最宝贵的东西」:「单纯」,「真诚」。
对于90后的成长,漫画是重要的陪伴品,《火影忍者》和《海贼王》几乎是每个90后必看的漫画书,但吴亦凡说自己唯一看过的就是《灌篮高手》,因为它和篮球有关。「所以我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我可能喜欢的就是只干这一个,打篮球就打篮球,其他运动都不关心。」吴亦凡说。
第一次通过篮球体会到自我表达的快乐的吴亦凡想要追随这种感受,他把进NBA当作人生梦想。但在母亲看来,打篮球是「容易受伤」的,「生命力比较短」的。
吴妈妈记得体校老师一直表扬儿子「是最好的后卫」,「而且他不抢,他总能在局里面,他从来不会说要我自己表现」,吴妈妈说。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那应该是吴亦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赞美自己、需要自己的集体,他想表现得更好。尽管相处时间不长,吴亦凡至今每年回广州仍要见一下这些曾经的队友。
吴妈妈最后是把儿子从广州「硬给他拉走」的。吴亦凡很伤感自己的梦想还没怎么开始就破灭了,「回去就特别难过,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梦想,而且特别舍不得,那个时候模糊有了一点自己的价值观和一些渴望追求的东西,但没办法,就是还得跟我妈妈回去,没有选择的余地。」年3月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他对主持人说。他把没有选择余地的原因归结为「因为自己太小了」。
吴妈妈记得儿子「回去的时候就很难过,有几天不出门」。有什么事情,吴妈妈都会把他硬拉出去,「那段时间的任务就是怎么让他缓过这个劲,」她说,「但那次我记得特别难。」
吴亦凡妈妈
吴妈妈和吴亦凡
想要自己承担自己的人生的感觉太强大了
吴妈妈把高考当做自己抚养任务过了大坎的标志。随着高考越来越临近,她也越来越紧张和严厉,吴亦凡记得那时母亲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会大吵,他把这个问题归结到了自己不会沟通上,因为自己是一个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人的人。
年11月,第一次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年轻的吴亦凡说出了关于人间关系的深刻的话。「单亲家庭比较现实的就是,其实母子关系比较容易走到一个极端的情况,因为没有第三个人和解。」
在这种极端环境中,有几次郁闷崩溃离家出走,走在家门外的小路上的时候,那是他特别希望有一个第三个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另外一个人来安慰一下她也好,安慰一下她就行了,其实我没关系的。」
这是引导他去韩国的主要原因。「我不希望跟她这样的,我好怕两个人的关系会变得没有以前好了,我特别担心。而且人长大了就会知道生气的人其实是最累的,说的那个人是更累的,而不是听的那个人。其实那个用心地去说你那个人会比你要累。(妈妈)本来就挺辛苦的,再这样心情不好其实对身体特别不好。所以我就去韩国了。」
还有让他担心的是,前一年因为回广州,他的学业有些耽误,他害怕自己会考不上大学。母子的花销是靠以前的积蓄,想到上大学又是一笔钱,他更恐惧了。母亲绝对不说经济压力,但是他感觉后面几年她压力变得特别大,压力通过「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要怎样」的句式传达过来。
吴亦凡特别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变成别人的负担。那段时间,他开始打一些零工,去餐馆洗碗,KTV端酒盘,尽管只能赚到一些零用钱,当自己的努力可以带来一些改变时,他感到生活中稀有的放松。
吴亦凡觉得母亲给了他很多正面的东西,「但这也没有阻止到我18岁要独立的这个想法,觉得一定要独立,我希望能够回报她,能够照顾她。」
吴亦凡从没有想过要当明星。那本是温哥华非常普通的一天,在同学的要求下,他陪他去了韩国SM娱乐公司来温哥华招练习生的面试,当听到「包吃包住」四个字时,去韩国当明星的念头一下子在他脑海中闪现,「各方面我觉得等于说能自己活了嘛。」他说。
合约虽然包吃包住,却长达10年,「妈妈觉得实在是……签完出来就30多了,最青春的时候。」但吴亦凡完全没有想这些意味着什么,他告诉《人物》记者,「我想要自己承担自己的人生的感觉太强大了。」
意识到儿子的坚决,是在签约过程中。吴妈妈至今记得她是到了机场才和儿子最终签的约,「我们娘俩都在哭」,她说,她记得儿子说妈妈我觉得真的对不起你,你养育我这么大,我让你这么伤心。「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说好,儿子没事了,那我们回家,回家了,这是我当时的回答。」她以为儿子心软了,接着,她听到的是:我签。「他就是流着泪把字签了。」
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