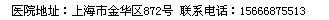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饮食调养 > 郝新光假枪毙吓不住俺娘回首往事都是眼泪
郝新光假枪毙吓不住俺娘回首往事都是眼泪
假枪毙吓不住俺娘
我母亲生于年,逝于年。
我妈妈没进过学堂,没文化,识几个字,不多,还是后来在队伍上学的。
"无知则无畏",三十几岁就当抚顺巿第二建筑公司党委书记的妈妈,什么事都身先士卒。那时候盖楼房,需要工人一锹一镐挖地基。生理期的妈妈也跟工人们一起站在水里挖沟,盖房子。不幸得了急性肾炎,到医院草草看了一下,又回来和工人们并肩战斗了。急性肾炎转变成慢性肾炎,在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又变为尿毒症,并最终要了她的命,享年五十二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妈妈是巿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领导阶级造起反来,折磨人的手段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妈妈抓起来,关在高墙电网的供水一厂。东北高寒山区的冬天,滴水成冰,他们扒光妈妈的衣服,让她跪在冰上。每条腿上压两块砖头,每只手还要举两块砖头。砖头一掉,就拳打脚踢。妈妈摔倒在冰上,他们就用钢鞭抽,蓐头发叫妈妈重新跪好。
他们拉妈妈在大卡车上游街,他们穿着棉大衣,捂着大口罩,戴着棉帽子。却只给妈妈穿着单衣,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二十多斤重的大牌子。妈妈脚下踩着凳子,车开站不稳,他们就用枪托砸,用脚踹。
领导阶级更会玩的是,每次妈妈到了生理期,他们不但不给手纸,还用枪逼着妈妈穿单裤坐在凉水池里。妈妈不从,他们就用口袋把妈妈的头包起来,乱棍打昏,再推到凉水池中。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逼妈妈自杀,好使他们指控的罪名成真。可妈妈山东人的犟脾气,呵,不对,共产党员的信仰,使她偏不自杀。她说:"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我就不死,我相信共产党有给我伸冤的那一天。"(可惜她没看到这一天)。
领导阶级没招了,玩起了假枪毙的把戏。他们扒光妈妈的衣服,把一个肿得已没有人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在流血的妈妈拉到雪地里,让她承认自己是假党员,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三反分子,不承认就枪毙。
我到现在都琢磨不透,是什么支撑着妈妈,她竟然能拍着自己的胸脯子高喊:"往这儿开枪吧,日本鬼子的子弹我没怕过,国民党的子弹我没怕过,你们的子弹我更不怕!"
他们看这招不灵,匆匆朝天放了几枪,把戏草草收场了。
我现在能挺平静地说这件事,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妈妈一连三个春节都不在家,姥姥挪着一双小脚,到供水一厂想看看妈妈。领导阶级手拿鞭子指着姥姥说:"臭不要脸的老太婆,养了一个走资派,死都活该,有什么好看的,不许见,滾!"
姥姥回来,忧伤过度,躺倒在床上。
十一岁的弟弟去看妈妈,领导阶级不让进。弟弟边哭边喊边往有电网的铁门上扑。他们就要进屋拉电闸,给电网通电。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来喊:"大光,快把弟弟拉走,他们什么亊都能干出来!"
我领弟弟往回走,鼻涕眼泪都冻在弟弟的下巴上。
我们姐妹三人同时被赶下乡,没有一个人到车站送我们。火车站人山人海,只有我们三人孤零零站在一起。没有多少行李,因为走资派的爸妈加一起每月只给开50元钱,去掉房租、水电、煤气费,维持家里人吃饭,连买几分钱一斤的苞米面都不够,没有钱给我们准备下乡的东西。
妈妈被折磨的多次昏迷,已经不能站立行走。领导阶级这才用个破代车子把妈妈送回家。我们见状,医院,医院说已没有治疗价值,不收。
我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医院都认为没有什么治疗价值的妈妈,靠什么信念支撑,在姥姥的精心护理下,过了几个月竟奇迹般地能站起来行走了,竟熬到了年春天。
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灾难深重的祖国百孔千疮。一天早晨,妈妈拿出自己过去上班拎的黑皮包,擦了又擦,装进去钢笔和笔记本,还让姥姥给她把饭盒装好,非要去上班不可。大家怎么劝都没有用。
妈妈推开门上路了。我实在放心不下,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妈妈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双腿,走得很慢很慢。走一会儿,就在马路牙子上坐着歇一会儿。平时几分钟的上班路,现在她走了四十多分钟了还没到班上。
我实在忍不住了,跑上前去,一把扶住妈妈,非要背她回家。谁知妈妈却说:"你们都不理解妈妈的心情呀,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想再为党多做点工作。"
妈妈上班仅仅三个多月,就与世长辞了。
说实在的,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妈妈。难道仅仅是信仰吗,信仰就能使妈妈扛住那常人难以忍受的残酷折磨,就能使一个垂死的人起死回生,坚持,再坚持,想看到伸冤的那一天,就能使一个人临死前想的只有为党工作。信仰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平心而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信仰共产主义,我还看过共产主义老祖宗的许多著作(这点比妈妈强多了),可妈妈做到的一切,我似乎都做不到。她留给我的是心底抹不去的痛和无尽的思索。
回首往事都是眼泪
我父亲生于年,逝于年。
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半耕半读近十年有点文化,曾在农村教过初小。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年出生时,他是八路军的山东省栖霞县县长。我母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年,十六岁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八路军的村妇救会主任。
我父母是怎么认识的,因二老的去世已无从考证。他们在世时,也没有时间跟我们谈及此事,因为他们都是"工作狂"。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们基本不见面。我还没上学时是这样:我没起床,他们已上班走了。晚上我睡觉后,他们才下班回来。我上学后是这样:我上学走了,他们才起床,我们晚上要睡觉了,他们才下班回来。
妈妈一口气,仅仅用了八年时间,就密集地生了我们姐弟六人(大姐出生乱世,寄养在老乡家,等解放后去找,这家老乡已人走家搬,谁也不知去向)。如果妈妈不做"结扎",在大好的新社会,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弟弟妹妹。
爸爸在家是甩手掌柜,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问,一日三餐都是送上楼他自己单独吃,和我们五个孩子没什么接触。姥姥对爸爸的评价是:你爸这个人好伺候,做啥吃啥,从不挑拣。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爸爸不改"农民习气",好不容易休息一个星期天,他又要垒鸡窝,又要砌院墙,安排我和泥。这个星期天没干完,下个星期天接着干。好不容易干完了,他不满意,推倒再重来,真是烦死人。院子折腾完了,又叫我们往二楼平台运土,他在平台围墙外垫土种菜,在平台围墙内钉木架养兔子。规定我们放学回家都要带一捆草回来喂兔子。
文化大革命中,爸爸挨批斗,戴高帽,挂牌游街,没有了当巿委文教部长的尊严,也不让有做人的尊严。当他到我们学校挨批斗时,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泪水只能往肚子里流。
不过,爸爸挨批斗只是那个年代的例行公事,跟妈妈比起来,不过是小菜一碟。
年,南征北战打天下的父亲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赶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爸爸下乡的苍石公社滩洲大队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条大河从村后流过,村前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滩洲象一个孤岛,只有冬天大河封冻时,汽车才能越过冰面,驶进村里。我们搬家的那年冬天,很冷很冷,冻得我脸色发青,上牙和下牙直打架。
老乡给我们的房子盖在铁路桥洞外,尽管层层叠叠的群山上长满了树木,我家的房子却没有一根木头。墙是石头磊的,房顶是杏条编成炕席状再浇点水泥胡弄上去的,薄薄一层,根本抵御不了高寒山区的低温。走进屋里,刷刷的冷,感觉和站在外面差不多。墙上结了厚厚一层霜,雪白雪白的,阳光照射上去,泛着耀眼的光。
爸爸拣来一些烂柴禾,拼命地烧炕,炕头烫得无法坐人,炕梢不温乎。我们坐在炕上,围着棉被,还是一个感觉就是冷。夜里睡觉,盖两床棉被,头上戴着大棉帽子,才能睡着。早晨睁开眼睛一看,被头上结满了霜花。真是不堪回首的岁月。
最苦的是打柴,屋里要拼命烧炕,才能有一丝热气。为了保证有充足的烧柴,再冷的天也要上山打柴。山上的积雪没到大腿根,为了不让雪灌到裤筒里,我们和爸爸都在家打好绑腿。爸爸给我们把镰刀磨快,绑在一根长长的细木杆上,我们和爸爸就拉起雪爬犁向深山老林出发了。
到了目的地,爬上半山坡,这时候,大雪几乎把我们腰以下的部分都淹没了。我们仰着头,高高举起绑着镰刀的长木杆,把镰刀头搭在落叶松树上的枯树枝上,使劲往下拽,枯枝断了落下来,我们把落在雪上的树枝收集到一起,捆起来,连滾带爬地捞到山下,装到爬犁上,等爬犁装满后,我们就把爬犁绳套在肩上,弯着腰,使出吃奶的劲拉爬犁回家。常常还走不到山口,我们就连饿带累走不动了。兜里一块宝贵的糖,是我们的强心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拿出来吃。靠这点宝贵的热量,我们才能把爬犁拉到山口。
在山口永远不变的是爸爸养的那条狗在摇头摆尾地迎接我们。它发现我们走来了,立刻就冲了上来,围着我们前后左右地跑,每当这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劲,一口气就能把爬犁拉回家。回到家,绑腿和棉喔啦鞋已经冻上,解不下来绑腿,也脱不下来鞋,真苦呀。
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艰难岁月,物质极端匮乏,饿死人是正常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让你苟延残喘就是天大的照顾了。家里什么也没有,整日不见荤腥,有糖尿病的父亲"很馋",他终于忍不住想吃肉了。家中唯一可食动物就是那条狗,父亲对它下了"毒手"。
没有杀过动物的父亲不知如何杀狗,他想用木棍把狗打死。腿被打瘸的狗,挣脱链子逃跑了。爸爸眼中流露出失望的光,自言自语地说:"它不会回来了,它不会回来了。"
这一夜,老爸出去好几趟,蹲在狗窝前看,狗都没有回来,爸爸死心了。
谁知天亮后,老爸想去收拾一下狗窝,被打瘸的狗却趴在窝里。爸爸喜出望外。这回他接受教训,把一条绳子系一个活扣套在狗脖子上,绳的另一端穿过埋在院子里拴晾衣绳的木杆上的一个铁环,父亲用力一拉,把狗吊起来,狗被勒死了。
那时候,父母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说一不二,孩子们在家是没有话语权的。虽然我们心里都不想让爸爸勒狗,但谁也不敢说出来,我们偷偷地哭了。
第二年,我们家养了一头小猪,我们天天上山挖野菜回来在大锅里把野菜煮了,然后喂猪。对小猪最关心的人是爸爸,老爸把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中间只有一排木栅栏相隔。我们每次上厕所,小猪就眼巴巴地站在那儿瞅着,爸爸也在屋里等着。等我们拉完屎,爸爸就用小棍把屎通过栅栏空隙扒拉到猪圈里去,小猪高兴得直啍啍,这是它每天的伙食改善。
小猪养了四个月,还没长到一百斤,爸爸就迫不急待地把它杀了。爸爸在房后的小山根处,自己掏了一个浅浅的小山洞,把猪肉藏在里面,用雪埋上(那时我们不知冰箱为何物,没听说过)。一个老走资派辛辛苦苦养的小猪,自己有病都舍不得吃,结果却被常到家里来看望的大队干部偷走了。贫下中农老师呀,就是用这种方式教育着也是农民出身,拎着脑袋打天下的老走资派。
不堪回首的往事,都是眼泪……
(写于年正月初五重返滩洲归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