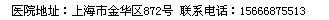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闭角型青光眼 > 疾病预防 > 古微饮一杯茶,听一段情
古微饮一杯茶,听一段情
点击上方 第二日下了早课,他一回头便发现那个一早晨都躲在他身后打瞌睡的师侄早就没了踪影,禁不住摇摇头,穿过长长的竹林回屋。却发现那个已然精神抖擞的小丫头早已在门口等候着他。 “师叔师叔,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吖,快走,陪我去集市买东西吖。”衣袖被小小的手扯住,他脸上微微发烫:“我要打坐了。”说罢再往前走,小丫头不依不饶的拦住:“师叔别打坐了,陪我去吧,师叔给我买糖葫芦吃,我就做竹笋给你吃怎么样?”他有些发愁的偏头望着那小丫头明晃晃的笑意:“拆招赢过我,我就陪你去。”小丫头歪头看她:“诶,师叔你欺负人诶!我要是打赢你,那你就得给我一辈子糖葫芦!”少年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起来,转身而去,徒留那个小丫头在后面师叔师叔的嚷嚷着。 “师叔?”小丫头从竹丛后探出脑袋,手中拎着一个食盒:“师叔你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少年放下书抬起头:“师侄,你也要好好研习才是。”小丫头笑嘻嘻的走近:“师叔你快尝尝我做的竹笋好不好吃?好吃的话吹笛子给我听吧!”少年无奈的笑一笑,摘下身侧翠绿的竹笛。 “师侄。”少年叫住离去的小丫头,从身后不知哪里拿出一支糖葫芦:“给你。”说着便又红了脸,小丫头脸上得笑意渐浓:“糖葫芦诶!我就知道师叔最好了!” “师侄,你要不要同我下山看看?” “下山吗?好阿好阿,那师叔就可以每天买糖葫芦给我吃啦!” “好。”
“陌苏,你回来了。”黄衣的少女撑着花伞,仰头看着匆匆走过模样俊朗的少年。
“嗯。”少年淡淡应一声,脚步不停歇的擦身而去。少女望着他的背影张了张嘴,最后却也只是失望的低下了头。 陌苏,你真的不知道,我喜欢你吗? 第二日,少女再来到陌苏家时,陌苏的母亲只说一句“陌儿他去拜访各地名仕,依姑娘你莫要再来,我家陌儿当有前途似锦。”少女低下头,摆弄着手中的花伞。 陌苏拜访各地名仕,想必是为了学习和积累,他那么努力,必是会中举,到时在京城做官,她这一场爱恋,必是无始而中。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有些盼望着陌苏无法考到京城,可念头一出,便被她立刻打散。她,那么喜欢他,又怎么会为了自己小小的渴望而祈求陌苏错过自己的抱负。 还是去京城吧,就当他,昙花一梦好了。她这样想着,这样去庙宇祈祷着,却是也恨自己为何不肯自私一些。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陌郎,陌郎,你可知我心悦你久哉? 来夏,陌苏高中的消息传遍了这个小小的城镇,每个人都喜笑颜开,庆祝这难得一遇的大喜。 少女坐在河边,玩弄着手中的柳枝:陌郎,陌郎,珍重,再见。 吾,心悦君已久矣。
他是下凡历劫的上仙,她是地狱中的鬼差。
在十三里曼珠沙华的花海里,他面似冠玉,眉眼如画,她黑纱附身低头沉默的领路。没有心的身体里却觉得好像有什么要跳出来一样。 她一见倾心,每天在茫茫花海等待着他历劫归来。 他归来之时,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还是十三里花海,还是她沉默的低头领路。 “小鬼差,生死簿在何处?”他突然发难,毫不客气的扼住她修长的脖颈,她沉默的为他指了路,看他毫不留恋的甩开她电一样的消失眼前。 她去了人间,强行将那女子已然转世的魂魄提回,正赶上他闹了地府勾了生死簿。 “给你,快走。”她沉默的将女子的魂魄扔进他怀里,反手推进轮回,回过头平静的等待她魂飞魄散的结局。
“你这臭和尚,本公主哪里让你看不上!”一身华丽宫装的女子气急败坏的跳脚,完全没有口中那一句“本公主”该有的端庄。眉清目秀的小和尚像是没听见一般,直径在蒲团上坐下,闭上眼睛开始了一天的功课。
“施主请回,我乃佛门弟子,如何娶施主为妻?”夕阳将落之时,小和尚将一路跟至禅房的女子拦在门外,“你为何不喜欢我?”她扯住他的僧服,有些凄苦的问:“我堂堂公主如何配不上你?你那普度众生的佛祖,为何不渡我?你为何不渡我?”小和尚沉默良久,慢慢的扯出衣袖,门在她眼前决然的关闭。 皇帝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最宠爱的女儿已经在寺院里住了大半个月,九五至尊勃然大怒,宠爱的女儿如何比得过皇族的脸面。她被以和亲的方式远嫁他处,他被以亵渎佛祖的罪名腰斩于市。 腰斩那日,他跪于闹市,好奇的望着尘世,这就是她生活的世界? 今生不负佛祖,却是负了她,负了自己。只愿来生不遇佛祖不负她,许她一生欢喜一世无忧。
她盘膝坐在地板上,拿起书看了几页又丢下,百般无聊的数着阳光透过树叶撒在地板上的斑斓。她歪过头去看窗外的街道,仿佛还可以看到他穿着肥大的校服笑容微暖的出现在街口,做着口型对她招手说“快点下来。” 她又回过头去看角落里的画板,画纸上少年挽起校服衣袖露出白皙的手臂,笑容青涩。她望着那个脸庞慢慢伸出手,却始终不敢触碰,只是一遍一遍低声念着他的名字。眼泪落在地板,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肖然,肖然…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名字如此平凡,对于我来说却好像一个咒语,无论何时,咒语一出现,就会打破我所有的坚强。 抬头看了看时间,她突然起身,换上挑选了很久的礼服画了精致的妆容,眼影遮住红了的眼眶,唇线勾勒出微笑的模样。 她望着镜子里镜子里容貌明艳却满眼悲伤的女人,慢慢咧开嘴,似哭似笑。 开车来到礼堂,推开门,在喧闹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西装革履的他。今天的他看起来格外开心,穿着西装的他比穿着校服的他看起来更加成熟英俊。 她走过去,望着深爱多年的男人,勾起嘴角:“肖然,恭喜我们终于实现了17岁的承诺阿。”男人抬起头看着她,亦弯眸笑起来:“你是说一起走进礼堂么?”他拍拍她的肩膀:“好了别闹,婚礼要开始了。” 她望着他,绝望渐渐弥漫了整个心房,她却听到自己戏谑的笑说:“哟,新郎这是等不及了?” 后台有人喊着“司仪快点就位!”她应了一声,转身拿起话筒走上礼台。 然后他挽过身边雪白婚纱的新娘踏上鲜红的地毯。 她笑着看他们一步步走向自己,却哭着看他渐行渐远。 肖然…祝你幸福。
眉黛远山,轻缈纱云。石桥上蓝衣的姑娘打着伞漫步,时不时向水中抛洒一点鱼食。“救命啊!有人落水了!”刺耳的喧哗,那姑娘循声望去,一个年轻的公子在水里浮浮沉沉挣扎不起。顾不得其他,姑娘跳入水中像一尾鱼般灵敏的游过去,带着不省人事的公子上了岸。好一番救援,终于缓过神的公子理了理衣服,站起来恭恭敬敬的向姑娘施了一礼。姑娘坐在岸旁,仰着头望过来,却看到那公子眉眼似画,气质如华。这样的小镇何时来了这般俊朗的少年?姑娘托腮看着,直盯的公子惴惴不安,面色绯红。姑娘突然就想起偷偷去茶楼听话本子里的故事了。她笑眯眯的望着人:“施什么礼,与其用这等繁文缛节来打发我,倒不如以身相许?”不料这话却吓得公子连连后退:“姑娘莫开这等玩笑,小生已有妻室,怎能…”这般说着,远处已经气喘吁吁的跑来一个少妇模样的女子,那女子一路跑来直直的冲进公子湿淋淋的怀里:“相公,我听隔壁大婶说这边有人落水…你,你怎么样?”公子温柔笑着安慰着女子,小心翼翼的隔开自己的湿衣服。姑娘突然觉得这一幕有些刺眼。再后来姑娘就每天坐在桥头,托着腮看公子拿着几本书匆匆来去。可公子再跟姑娘说话已是一年以后,那天阳光很好,公子和他的娘子一起踏春而出,路过河畔时那女子失足跌入水中。“姑娘求你救救在下的内人!”可这一次姑娘只是站在湖畔摇摇头,她拒绝下水救人,还拦住了几次想跳下去的公子。“命该如此,你救不了她。”她说的本是事实,公子却狠狠的拂开她的手骂上一句“恶毒”。她被甩在地上,抬起头却看到公子狰狞而悲伤欲绝的脸。她突然想起第一次遇见他,他弯腰施礼,风度翩翩。他的娘子,当真是他极为重要的人吧…姑娘至此就消失了,桥头再也没有打着伞哼歌的姑娘。过了几日,被湍急的河水冲到不知所踪的女子步履蹒跚的回来,把正要建衣冠冢的公子惊喜的不知言语。女子说,她过奈何之时,被湖畔桥头的姑娘拉住,硬生生的推了回来。可进了阴府的人,又怎么能回来呢?公子连忙赶去桥头。日日站在桥头的姑娘不见了,一个少年站在那里,恭恭敬敬的向公子施了一礼:“姑娘在此方做了千年河神,正想去人间好好走走,索性顶了你家娘子,公子且请安心。”公子终于安下心,感恩戴德的回了家。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去不久后,那少年身后便钻出一个更小的少年,他哄着眼睛问:“阿哥,姑娘明明为了救那女子违反了天地因果,连魂魄都要被打散了,姑娘为何不告诉他?”那少年揉揉了他的头发:“大概,是不愿他有一点难过吧,哪怕是愧疚都不愿。”他想起最后一次看到姑娘,她一身狼狈,满身伤痕,却笑的欢喜明媚…
杀神临世,她惶恐,抬眼望向那神邸。分明是神,然肃杀毕现。
“殿下,莫杀我,我…我喜欢你”他嗤笑:“喜吾,为何?”“因为殿下漂亮”他掳她而去,终没杀她,却也未管。众仙重修太上镜,以困唯一杀神。太上镜开,她顶身而上:“我喜欢殿下”看着她消失的背影,他低喃:“为何?”天际传来幽幽声音:“因为殿下…寂寞”仅百年之余,杀神以己之力,破上古神物太上镜,自中救出她。她只虚弱的笑:“我喜欢殿下”“为何?”“我在里面每日看见虚镜与炼狱,虚镜是你,炼狱里没有你。”他默然,将她一身污秽挥去,送至仙界:“你之感情,让吾困扰”。转身,直奔九重天外。
他出关。“殿下,那女子已在门外等了百年”眸光微沉,他无风自动,殿门大开,门上两条赤龙均乖顺。她抿嘴“我喜欢殿下”“吾早已知晓”“我仙骨已剃,惟余此身。”他默然叹息,伸出一手将她虚扶起,转身走进殿内,她紧随其后。“殿下还困扰吗?”“我喜欢殿下。”“杀神本无喜乐。”“可殿下在笑”“识破吾,你很得意?”她点头:“得意”,良久笑意隐去,她微微上前,虚抚着他眉心处:“这里可还痛?”眉心处原有一抹红色滴子,她曾剜下它,铸了太上镜。此处只余一道疤。却终是悔了。他摇头,却终是轻笑出声。杀神有妻,其妻终极一生,无半点法力,却是半神之躯,只知,其妻曾是仙界重臣。
第一次见他,我为他芳心暗许,他对我一笑留情。
第二次见他,我为他心跳如雷,他为我轻托茶展。第三次见他,是我的洞房花烛,他对我锁眉,转身。我成了冷妃。我是一个哑子,可他不过一个落魄皇子。第四次见他,他身后跟着我的妹妹,于是真相大白。第五次见他竟已是半年之后,他身后跟着我的哥哥,迎他回京,二人一眼没有望向我,可能他们不知道,那年火灾,是我将他与相公拼命搬出,满背伤疤,灼烟坏了喉咙。他们只知道最后脸部被毁容的妹妹趴在相公身上哭泣的身影。可我什么都说不得,妹妹是牵制相公的风筝线,而我是为家族铺路的棋子。第六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皇帝,兔死狗烹,我从冷妃变成了废后,家族里,除了妹妹,皆为庶人,包括我,他是个仁慈的皇帝。只是我始终皇帝的女人,出宫已不可能,即使我还是个处子。第七次见他,是在妹妹得封后大典上,只是,妹妹终究没有成为皇后,大典被废后毁了。第八次见他,我举着火把,要挟着那些嚣张的奴才,才叫来的他,他皱眉看我,我当着他的面,将冷宫点着,他没有救我,他定以为我在玩把戏,只是我是真的活够了。然后,我竟然看见了飞奔来的哥哥。我这一生第一次在一个人的脸上看见担忧的表情,只为了我。我竟喊了声:“哥哥”。我如今我住在云山下,和哥哥。只是总会出现一个穿着锦袍的人。我跟随着哥哥一同下跪,却总是看见他紧锁着眉头,我不识他,我怕他。
第一次见他,是在云山脚下,我对他惊悸非常,他对我似乎厌烦,眉头紧锁。
第二次见他,是在家中,哥哥俯身拜他,我知晓他是当今圣上,叩首跪拜,只看见他的双手微颤。第三次见他,是在小镇的集市上,阿婆与哥哥为我拉了红线,我知晓自己年岁已大,不敢挑剔,只是在途中被他掳去。第四次,没有第四次,因着我日日在宫中见到他,他对我说宫中于我无禁地。我径直走到了一个外观有些黑旧的宫殿,只觉得前世见过一般。他却白了脸色,伸手拉我便走。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总是卧榻在那个旧房子中,似乎有浓厚的安全感。然后我看见了青着脸色的哥哥,我欢笑上前,这些年,其实我只会说“哥哥”两个字,我依旧,是个哑子,而他是皇帝。后来哥哥走了,我看见了一个半边脸毁掉的人,旁人告诉我那是他的废后,我突然想起曾经有一道明黄色的圣旨被掷在地上,大大的“废后”二字占满了眼眶。原来,这里我果然来过,兜兜转转,重新回到起点。我请求出宫,他没有应允。最终各退一步,我回到了以前的冷宫,只是冷宫早已变得辉煌,御书房竟被全数搬进了冷宫之中。似乎是一场报应,我的封后大典上,妹妹来了,只是大典没有被毁,哥哥带走了妹妹。第二次洞房花烛,我不再是原来的黄花闺女了,只是第二天,看着身旁的睡颜,我竟喃喃叫出他的名字,随后看见他惊悸的双眼······
“紫檀,我喜欢你。”
“紫檀,你抬头看云。”云形缥缈,隐约几个大字“我喜欢你”。“紫檀,这串铃铛,我好喜欢。”“滚——”他终于开口,却是狠狠地将她手中的铃铛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她笑容一怔,声音已喃喃出口:“对不起——”却只来得及见到他离开时的紫色长袍在风中飒飒作响。她是祥云散仙,他是魔界至尊。传闻魔尊欢喜过一名仙界宫娥,只是那宫娥早已香消玉殒,并非死亡,而是,魂飞魄散。从此魔尊,恨极天人。“紫檀,这是——”未及说完,便已住口,双眼惊异的看着面前的景象,她知,那是活祭,违反天伦,逆天改命,天劫难逃。冷冷斜睨了她一眼,只是伸手一团火球打向她,云朵惧火,索性他只打到了她的脚边。“又来做什么?不要摆出你们仙界那一副假仁义的模样。”她微颤:“紫檀,我喜欢你。”他却只是嗤笑:“这般轻易说出的喜欢,你相信吗?”语毕,将体内的魔力竟源源不断的注入那活祭中。她静默半晌,沉静转身,再没出现。九九八十一天的活祭,只是熔铸了那女子的肉身。天地变色,隐隐几阵阴风盘旋在魔宫上方,随后天雷紧随而至。他讽刺勾唇,竟是照单全收,天意似恼,最后一记夹杂着怒气,竟是有着毁天灭地的能力。他终于变了脸色,慌忙上前,隐约看见一抹白色的小东西在空中飘着。他惊悸,不想竟是她。天气渐渐放晴,空气中只隐隐弥漫着焦灼的味道以及女子缥缈的声音:“其实那句话,并不容易。”似乎痛苦闷哼一声,方才继续说道:“即便你法力再高,得到了也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紫檀,收手吧,祥云只可护你一次。”
我是老君兜率宫门上的一个门环,老君闲来无事,指点我一番,我竟修了仙身。
那日天帝自我面前走过,身姿卓绝,似乎巴望太久,我的真身从门上掉落,滚落到天帝脚边,天帝拾起我:“铁东西竟化了灵,不如跟我去吧。”我从没有见过这般淡漠而温润的笑,只呆呆点头。然后我被带到了凌霄殿,挂在了天帝的寝宫前。瑶池会上,天帝搭乘龙撵,我被他带在手腕,一同前往。魔尊紫檀因着祥云散仙攻入仙界,似要夺取散仙真身。然后我听见一声:“去吧”像第一次那般淡漠而温润。随即身体被强大的力量推出。在飞向魔尊的时候,我在真身中回头,茫然看向那上座的天帝,只觉那般遥不可及:“天帝,我好像…倾慕于你”只是身体已随魔尊坠入冥界,魔尊手中始终托着一朵浮云。那是我重新开始的地方。此时我才知晓,那年司命神君说的那句话:“本事铁石心肠,偏生要渡情劫。”
他一袭白衫,手执檀扇,将她望着:“这是哪家小丫头,好生俊俏。”
她虽涨红了脸,依旧不甘示弱瞪着圆眼将他望着。那一年的春光里都洋溢着幸福,她于他妻。硝烟起,战事发,他冲锋在前。人道战神将军沙场自战马坠落,竟能取了敌方首级。可她只担心他身体可还安好。一骑绝尘,将军夫人奔赴沙场,好一个夫唱妇随。大军全胜,只是战神将军魄力还在,人却痴了,只认得胯下坐骑。她弃红妆,着一袭白衫,手执檀扇,将他望着:“这是哪家公子,好生俊俏。”
她问过他一句话:“对你来说,我算什么?”沉默良久,他终于回答:“最锋利的刀刃,最合格的棋子。”她笑的花枝乱颤,摔门而出,我与你用心,你与我用心计。天下尽在他手,江山初定。她问他:“于你,我算什么?”他将她望着:“朝堂的安生,天下的稳定。”她微抿唇,嫁与他为妻,至此,女将为后,兵权集于圣上。万臣上表,填充后宫。她问他:“我算什么?”“一国之母,朕之后。”她对以往生死缄口不言,后宫万千,她笑以对之。天下安定,人道圣上天尊。她找到他:“圣上。”他抬头。“那年平南战场,我以身为盾救圣上一命,圣上曾允我一个条件,可还记得?”他沉思,良久点头:“难道你得到的还不够?”她微笑,摇头:“皇上,臣妾恳请离宫。”满室寂静,他指尖微颤:“为何?”“这囚笼,已经囚不住妾的心了”她叹息。“朕于你,算什么?”他问。“主人。”